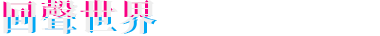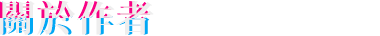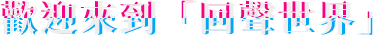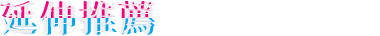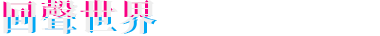
你已經死了,
歡迎來到「回聲世界」!
走在一片荒蕪之中,布洛迪還是無法相信自己已經死了。他記得身為FBI探員的自己正要追捕那個在兩週內奪走18條人命的恐怖分子。他記得珂蕾兒,今天早上他剛從她的枕邊醒來,他好愛她。他還記得那場爆炸,他被震飛拋上天空……他死了,真的死了。
他來到一個被稱作「回聲」的地方,這裡是真實世界的幕後空間,就像個檔案櫃,裝著和布洛迪一樣死於意外的人,原本可能擁有的餘生則化作無形的能量。這裡沒有法律和衰老,沒有火,沒有熱,沒有電腦或手機,而最讓布洛迪痛苦難耐的,是這裡沒有珂蕾兒。
他多麼想念她迷人的微笑,多麼想念那些他們共度的夜晚,當回憶持續啃噬布洛迪的心,他再也忍無可忍,為了再見心愛的人一面,布洛迪發現自己什麼都幹得出來。據說只要讓身上的能量變強,就能再次看見人間的景象,而增強能量只有唯一的辦法,就是──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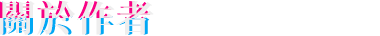
馬可斯.塞基 Marcus Sakey
1974年生,美國密西根州人,婚後與妻女定居在芝加哥。他在密西根大學主修傳播和政治學,也曾參加哥倫比亞芝加哥學院的創意寫作課程。塞基以芝加哥藍領階級為背景創作犯罪小說,2007年以《The Blade Itself》正式出道,一鳴驚人,不但榮獲《史全德》雜誌評審獎,並入選《紐約時報》編輯選書和《君子雜誌》年度5大好書。
他的作品曾入圍巴瑞獎、安東尼獎、黛利絲獎、麥卡維帝獎、ITW驚悚文學獎、普羅米修斯獎、Goodreads讀者票選獎、《犯罪狂熱》雜誌小說獎、《浪漫時代》雜誌書評獎等超過15個獎項,其中《異能時代》三部曲更獲得「愛倫坡獎」年度最佳平裝本原創小說提名,作品總銷量已突破200萬冊。
塞基筆下的文字極富畫面感,劇情高潮迭起,令人欲罷不能,多部作品並已售出電影版權,而《回聲世界》也將由奧斯卡金獎名導朗霍華執導,備受各界矚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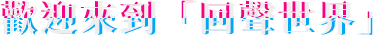
1
他出生在擁擠的街巷裡,這裡空氣惡臭,充斥著魚腥味,垃圾滿地,更夫沿路高喊:注意時間,小心門戶。那年是一五三二年,地點是倫敦。父親天涯飄零,母親幾乎不記得,他在街道上長大,有零工就打零工,沒零工就偷拐搶騙。那個陰天他頭一次看到「普西芬妮號」在太陽光圈中上下起伏,他就把這艘船當作了別人應該給他的承諾。
他的體型單薄,皮膚蒼白,心性浮動。不明白為什麼有人生而富貴,有人卻生而為奴,而且他也不肯認命。愛德蒙看著帆船卸貨,看著水手踉蹌下船,其中有一個不比他大的學徒。他跟著他們去了一家污穢的酒館,酒招是個船錨形狀,他們灌下一加侖又一加侖的加水啤酒。後來小學徒到巷子裡去小便,愛德蒙就一刀刺入他的後頸,往上一挑一扭,結果了他的性命。
隔天,「普西芬妮號」啟航,換了一個新學徒。愛德蒙工作勤奮,又笑口常開,大家都喜歡他,傳授他各種門道。他睡在甲板上,不是被踢醒就是被罵醒,一睜眼就看到明亮的陽光,呼吸到新鮮的空氣,生平第一次,他領略到何謂快樂。他學會打繩結,也挨鞭子,吃醃牛肉和爬滿了象鼻蟲的餅乾,看到了新世界,也發現不怎麼樣,也不過就是陸地、樹木和褐皮膚的人。
返程第二個星期就遇上了暴風雨。天空黑壓壓的,海面卻是一片白色泡沫,而且他們不是橫渡波浪,反倒是朝浪頭衝,爬升到翻湧的浪尖上,懸空個一秒,再墜落到谷底。愛德蒙聽見「普西芬妮號」嘶吼,看著水手長隨著主桅一塊被掃到船外,後來有一道和倫敦塔一樣高的大浪湧來,遮天蔽日,他把自己綁在前甲板上,想禱告,又覺得多此一舉。
他醒來後只看見一個洗得乾乾淨淨的世界。陽光熾烈,海面如鏡,「普西芬妮號」吃水深,損傷嚴重,主桅與風帆以及大多數的船員都不見了,乾淨的雨水倒是很多,可是船艙破裂,貨物和補給都不見了。
船長在暴風雨中壓傷了胸膛,高燒不退,彌留了兩天,不時向上帝呼號,上帝可能聽見了,所以第三天早上他就死了。剩下的七個人面面相覷,人人的心思都一樣,只是誰也不敢說出口。
曾經破壞他們食物的老鼠成了他們的食物,但沒多久連老鼠都吃光了。
又挨了兩天餓之後,理髮師和廚子把腦筋動到船長的遺體上。人人都吃了,只是吃的時候誰也不敢看著別人的眼睛。
可是愛德蒙天生就不是個省事的,他知道船身破裂,又沒有帆,想要找到陸地可是漫漫長途。肚子填飽了,他的心思也敏銳了,知道只要有心,船上還有很多肉可以吃。
理髮師被人在船艙發現了,手上握著剃刀,喉管割破了。這是下地獄的大罪,大夥都同意。但吃的時候大夥都沒有遲疑,只是仍然不敢看著別人的眼睛。
「普西芬妮號」就這麼漂流著,任憑潮流和上帝宰制。
過些時日發現左弦的繩索纏住了一個淹死的水手,大家都說他一定是晚上掉下去的。大夥匆匆禱告了幾句,廚子就動手了。
陸地仍然遠在天邊,陽光仍熾烈,而且一絲風也沒有。
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殺,水手一個接一個倒下,最後只剩下了兩個人。廚子說這是上帝的懲罰,所以他們得終身漂泊,為吃人肉而付出代價。
愛德蒙也認同,於是兩人禱告,祈求上帝寬恕。
愛德蒙殺了廚子,用的是那把讓他登上「普西芬妮號」的刀子。他觀察過廚子分屍,所以儘管是第一次,他覺得自己做得還不賴。他把人肉醃的醃,燻的燻,瞪著海平線,吃著恐怖的口糧。
暴風雨侵襲已經是幾週前的事了,而愛德蒙也又漂流了好幾週。
他已經很久沒東西吃了,被太陽曬得精神錯亂,忽然有天早晨他在甲板上抬頭,看見了陸地。
他死了,距離陸地還不到一哩。
⊕
其實並沒有那麼不一樣。
愛德蒙涉水到岸上,雙腳踩著陸地,身體卻搖搖晃晃。他站在那裡看,等待審判。漫長的幾週來,唯有陽光和海水以及因飢餓而肚子絞痛,現在他等待著天使的合唱或是張牙舞爪的魔鬼。
結果他等了個空,而且也沒等到別的靈魂。海水輕拍著海岸,微風吹動高聳的樹木,一道淺淺的小溪涓涓流入沙灘。
灌木叢上長滿了紅色漿果。
愛德蒙撲了上去,把一把又一把的漿果塞進嘴裡,接著又趴下來汲飲滲流的冰水。吃飽喝足之後,他翻身平躺,心裡想的是神父們實在是沒見識。數不清多少次了,他靠神父的施捨果腹,為了一點麵包屑就答應要獻出靈魂,而且總覺得自己還占了便宜。而現在證明了他果然是對的。
最後,他邁步出發。
一邊是鹹水,一邊是森林,大海他很熟悉,樹木卻教他害怕。他是倫敦長大的孩子,沒見過這種景色。綠色植物長得如此高大緊密,樹下淨是最清涼的陰影,樹葉縫隙吹出來的風都像在低語,召喚他:靠近一點,迷失自己,讓他滿口是沙塵,讓樹根從他的胸口長出來。
天空變幻不定,卻也是同一片天,太陽始終是淡淡的一塊斑點,從這頭的地平線移到另一頭的地平線。天空沒有海鷗翱翔,長草叢中沒有蟲聲唧唧。他獨自一人在死亡的國度裡遊蕩。晚上厚厚的雲層遮星蔽月,黑暗傾瀉而下,讓你伸手不見五指。他睡在海岸邊,在積累的針葉和樹葉堆裡瑟瑟發抖。
過了幾天,他發現了一條寬敞的河,緩緩地注入海洋,河邊有一圈圓頂茅屋,隱沒在矮林中。小村落既沒有炊煙也沒有聲響,彷彿廢棄了,彷彿某個被遺忘的種族為了自己的滅絕而建立了這裡,以資紀念。愛德蒙躲在大岩石堆後面觀察了一整個下午,一個人也沒看到。
茅屋蓋得很巧妙,使用彎木,以繩索固定,編草屋頂。屋內處處是野蠻人的物品,陶鍋,動物皮毛製成的衣服,奇異的多種子植物。他想像著茅屋中的生活:一個婦人在做飯,胸前吊著孩子。他幾乎能看到她在搗穀子,突然停下來;幾乎能看到她瞇起眼,看著他所站之處,不明白為什麼兩手變得笨拙,乳頭從一張嚎啕的嘴巴裡掉出來。
愛德蒙從樑上摘下了魚乾,坐在門口,看著天空變暗。心裡想著聽過的那些死後世界的故事,很奇怪為什麼會有人相信。因為唯有走過這一趟的人有資格說話,可就連他都不敢肯定,因為誰知道這一個蒼白多雲的地方就是終點呢?那些自稱懂得的人不是傻瓜就是騙子,一個也信不得。因為就憑愛德蒙的所作所為,他一定是該遭天譴的,可是眼前這一切卻哪能算是懲罰呢。
他睡在蘆葦床墊上,蓋著一床鹿皮斗篷,知道床上不只他一個人。雖然他看不見,摸不著,嗅不到,不過一定有一男一女也在床上休息。只不知他們的夢是否受到打擾。
他睡著了,醒來卻置身地獄。
一隻魔鬼色迷迷地低頭看著他,它是人形,腦袋瓜上卻長著羽毛,嘴巴咕嚕響,聲音發自喉部,牙齒也嗒嗒響,齜牙咧嘴。愛德蒙歪歪斜斜地向後退,看見在它後面還有其他的鬼怪,上半身赤裸,褐色的沉重的乳頭垂吊著。男魔鬼舉起了長矛,愛德蒙完全是走運,及時掀開了鹿皮,迎向了矛頭,鹿皮的重量拖住了矛頭,給了他空間向前躍,抽出刀子插入魔鬼的胸膛。
鮮血噴飛,而就在熱血的洗禮下,愛德蒙再世為人。
他是一名以烏龜為圖騰的烏拿拉胥提勾族人,跟其他兒童在樹林裡奔跑,賭博吵架,學習設陷阱布網罟,捕魚捉鳥。
他漸漸長大,看著婦女種植玉米和南瓜,同時強烈渴望,也發現他的瞪視得到了回報。
在明滅不定的火光中,他撫摸他的新婚妻子。他進入她時她頸部的麝香,小腹上的汗珠,緊抓住他的手勁。
在一陣乾淨冰冷的大雪中,他雙手抱著新生的兒子,感嘆造物者的偉大。
大熊散發出戾氣,是仇恨與憤怒的化身,即使在他疾奔向前救援他的女人時,一隻巨爪一揮,就把她撕成了兩半,利牙尖爪,呼吸濕冷,猶如從鳥的骨架上撕下滴著油脂的肉,而每一爪都像是抓在他自己的身上……
愛德蒙站在帳篷裡,又變回了他自己。他剛才的肉身倒在地上,而他的妻子驚恐地瞪大眼睛。
這一次,她說出奇異的嗒嗒語言,他聽懂了。
她在詛咒他。
一段人生,就在一瞬之間。一段故事有如一塊肉般囫圇吞下。愛德蒙因為它而紅光滿面,被它填滿,從內在發光。
他看著女人,想起滑入她熱熱的核心。想起了從前較強壯的男人拿他消火,有的付錢,有的不付。
女人必定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奪門而出,沒穿鞋的褐色腳底一閃即逝。
他微微一笑,沿著打獵小徑追逐,深入他再也不怕的森林裡。
就算這裡是地獄,他也會把它當成家。
2
芝加哥變得很陌生。
布洛迪應該是駕著汽車,停停走走,對計程車按喇叭,對騎車的人咒罵,而不是油門踩到底,在街上橫衝直撞。
人行道上應該擠滿了通勤族和觀光客和學生,人群應該從轉角溢出,腦袋隨著耳機搖來晃去。保母應該推著嬰兒車,遊民搖著杯子乞討。滿街人拎著俗麗的購物袋,牽著小狗,還有人問你有時間聽聽綠色和平組織的活動嗎?
可是人行道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斑馬線也空空如也。
只有三兩個行人不規則地行動著,企圖同時眼觀四面。布洛迪的輪胎吱嘎叫,一名穿上班套裝的女性立刻趴倒在水泥地上,雙手抱頭。
他飛馳過傑克森街上的殼牌加油站,整個地方都用藍色的防水布覆蓋住,塑膠布在十月的風中波動。大多數的加油站都這樣,像是精神病患包的聖誕禮物。
再過兩條街,一列橘線火車駛入上方的月台,沒有人上下車。車門關閉,橘線向北而去。
一所小學向後飛逝,他看見有輛軍方的悍馬停在人行道上,理著小平頭,穿防彈衣的人在守衛,自動步槍對著地面。公園的遊樂設施上看不見兒童,鞦韆隨風搖盪,彷彿有鬼。
他把油門往下踩,引擎的轟隆聲與來自四面八方的警笛聲融為一體。芝加哥警局忙著改進路障,布下了一張同心圓的羅網,擋住任何攻擊。理論上這個點子不壞,可是他痛恨這種被動的性質,這種投降的暗示……
到了。
這個路口寬敞,商家也多,有一家銀行,星巴克,飯店。西北角有一家馬利阿諾商行,近幾年才興起的,供應西環公寓的民生用品。
布洛迪住在新的西環公寓區,對這家店很熟。三層樓,玻璃與白磚建築體,一樓泰半闢為停車場,頂上有覆蓋,周圍有籬笆。一條小巷中央停著一輛警車,藍光投下刺眼的陰影。他在警車後急停。十來個人繞著圈打轉,像貓一樣緊張不安,不時轉頭避開明亮的日光,看著圓心的形體。
「讓開!」
旁觀眾人的圓心裡躺著一個女人。她仰天而躺,一條腿彎折的角度很奇怪,胸口有凝結的血液,一個警察跨坐在她身上,奮力按住傷口,同時俯身幫她做人工呼吸。她的購物袋掉在地上,雜貨散落,蘋果香蕉咖啡、一個冷凍披薩、一桶香草冰淇淋因為撞擊而掀掉了蓋子。
第十七個。
這一槍命中要害。上一分鐘她才從雜貨店走出來,肩上揹著帆布環保袋,手上拿著車鑰匙,下一分鐘胸口就炸開了一個洞。
當時她是在想晚餐要煮什麼嗎?是在期待見到先生孩子嗎?還是憶起了某部電影的一幕?
她也可能正想著那個馬上要殺掉她的那個人。
人人都知道芝加哥是個大城市,被鎖定的機率微乎其微,可是人人又直覺認定自己是目標。恐懼心態就是這種效果。恐懼會扼殺較高尚的動機,愛情、思想、創意,植入根深柢固的害怕。把人類變成野鼠,四處亂竄、尋找掩蔽,唯恐老鷹的利爪落在自己身上。
這樣的墮落讓布洛迪的憤怒幾乎可比那些兇手。
「你是誰?」警察是條彪形大漢,小腹把防彈背心繃得緊緊的。名牌上寫著J.索科洛夫斯基。他掏出了佩槍。
「威爾.布洛迪,聯邦調查局。」他以左手去掏證件。「你是第一個到現場的?」
「我們停下來買咖啡。」索科洛夫斯基正要用手槍去比星巴克,被布洛迪一把攔下,說:「嘿,把槍收起來。」
「嗄?」警察臉紅了,把槍插回槍套。「喔。」
「你看見什麼了嗎?」
「沒有,跑過來的時候只聽見槍聲。」
布洛迪轉頭看著四周,衡量視線,在黝黑的窗戶間尋找閃光。並沒有盯著什麼看,只是瀏覽了周遭一遍,看是否有什麼突出的地方。這種瀏覽的方式是他出任務培養出來的方法,每樣東西都需要評估它的潛在威脅。宣禮塔並不是為了讚頌阿拉而建的優美高塔,而是狙擊手的巢。蜿蜒的街道也不是如詩如畫的歷史遺跡,而是死亡陷阱,子彈會由牆頭飛過來,而且隨便哪家窗戶都可能會伸出一把自動步槍來。警笛大作,直升機的螺旋槳越來越近,芝加哥越發像是伊拉克的費盧杰,而不是他認識了一輩子的家鄉。
真是夠嗆,布洛迪心裡想。一個擁槍自重又喜歡戲劇效果的傢伙對文明居然有這麼大的影響。
⊕
九月十九日,兩個小時內有四人遇害。
潔莉.辛普森,護士,三個孩子的媽,邊玩「糖果傳奇」邊等橘線列車。可能連槍聲都沒聽見。
而邁可.狄爾曼卻拖了十分鐘才死亡。他太太打的求救電話一直不斷重播。
賴瑞.王正在替他的計程車加油,一顆子彈貫穿了他的喉嚨。
麗亞.庫馬醫師在美麗的秋日享受片刻的閱讀之樂,要不是病人取消了預約,她可能就不會送命。
四名受害人完全沒有關聯,迄今為止的十三名受害人之間都沒有關聯。狙擊手既沒有發布宣言,也沒有什麼要求。既沒有調侃警方,也沒有寄給媒體什麼加密的信息。而無論是伊斯蘭國或蓋達或白人優越論團體都沒有出面宣稱他是成員,採集到的DNA證實了兇手是男性。如果他是恐怖分子,也沒有什麼理念。
他只是殺戮,隨即消失無蹤。
或許恐懼就是他的理念,布洛迪想。而且他贏定了,他照著他的想法重塑了我的家鄉了。
「各位。」他轉頭向著人群,高舉著證件。「我是聯邦調查局的威爾.布洛迪探員,有沒有誰看見了什麼?」
人群看著彼此,又看著他,惴惴不安地看著天際線。
「隨便什麼不尋常的事情都可以,開得過快的轎車或是卡車,不太對勁的洗窗工人,一縷煙。」
「我看見她倒下來。」有個女人說。手指頭動個不停,像在捻念珠。「我們同時走到門口。」她陡然間瞪大眼。「喔,我的天,喔,我的天啊。」
「女士。」布洛迪朝她過去。「妳看見了什麼?」
「我……我們同時走到門口,我請她先走。」她像有狂躁症,講話像機關槍一樣快。「她對我微笑,我讓她先走。如果我沒讓她,我就……她就……我不知道會出事。我只是禮讓她,我不知道……」
「不能怪妳。」布洛迪按住她的肩膀。「人不是妳殺的。」
救護車響著警笛在停車場倏然停住,門打開來。跨跪在女人身上的警察站了起來,長褲被血染紅了,手上的鮮血也一直往下滴。兩名救護員衝過來,一個拿著人工呼吸器,一個推著輪床。
布洛迪知道來不及了。女人已經死了。無論她懷抱著何種希望,都被奪走了。組成人生的許許多多小片刻不再是她的了。她再也讀不完正在讀的那本書,再也不會打電話給她的母親,再也不會看週日的《紐約時報》、吃壽司、看電郵。五分鐘前她還是個人,現在卻什麼都不是了。
「怎麼會這樣?」索科洛夫斯基的臉色蒼白。
「開始記錄姓名。」布洛迪說。「沒詢問過的人不准離開。」
微胖的警察點點頭。
空氣彌漫著廢氣以及血腥味,更多警車抵達,直升機在頭頂盤旋,有如蜻蜓。救護人員把女人抬上了輪床,蓋上了白布。
布洛迪走向她倒地的地方,從雜貨中抄起了她的皮包。皮包裡裝滿了各種日常用品,像是人生的小小縮影:太陽眼鏡、手機、鑰匙、營養棒、護唇膏、口香糖、乾洗手、耳機。他掏出了她的皮夾,駕照上的姓名是愛蜜莉.瓦特金斯。照片上的她露出羞澀的笑容,半是和煦半是調皮。看起來像是練習過的笑容,可能是只要有鏡頭對著她,她就會換上這種表情。她的手機有密碼,不過他敢說,如果他打開相簿,她絕大多數的相片都會露出同樣的笑容。地址在艾伯丁街,就在摩根街的兩條街外。他們曾是鄰居。
在槍擊發生後的五分鐘內,停車場可以說亂成一鍋粥。警察詢問目擊者希望這一次至少有人能看見什麼。一排警員擋住了一群圍觀者,他們大都掏出了手機,錄下了屍體送上救護車的過程。人類對醜惡的興趣始終讓布洛迪感到困惑、好笑,甚至是氣餒。嘿!快看,她的血流到融化的冰淇淋裡了!快點,貼到網上。
他搖搖頭,走向救護車。一名救護人員在車子裡,調整輪床的前端,另一人在車外推輪床的尾巴。他前傾去固定輪床,脖子上的聽診器滑了下去,他一彎腰就把聽診器接住了。
就在此時,救護車的煞車燈碎裂。怪了,因為他壓根就沒碰到……
布洛迪一把揪住救護員的肩膀,把他往旁邊拽,他一臉吃驚,這時狙擊的槍聲也隨之響起。救護員絆了一下,摔倒了,整個人趴在地上。布洛迪也俯衝,姿勢彆扭。不知什麼在他背後呼嘯而過,很像一隻憤怒的蜜蜂。第二發子彈只差了幾吋,不到一秒鐘就傳來了粉碎聲,遠處不知什麼被擊中了。他結結實實撞到地面,極不優雅,卻一點也不感覺到痛。有人尖叫起來,圍觀的人互相推擠,紛紛趴下。警察跪在警車後面,掏出武器,瞪著四面八方。救護員背抵著輪胎,像螃蟹一樣爬,很好,他讓開了路,這下子布洛迪可以手肘和膝蓋並用,低著頭,從救護車底下看出去……
遠方連續閃出亮光,一、二、三、四、五,數到五時,第一發子彈也擊中了救護車的車身,砰的一聲,緊接著後面四發。子彈是由小巷子射出來的,小巷藏在三、四條街外的兩棟低矮的建築之間。
逮到你了。
布洛迪站起來,抓住救護車的邊緣,借力使力,拔腿疾奔。他繞過一輛警車,躍上了另一輛的引擎蓋,跑過去,皮鞋踩得金屬蓋咚咚響。他跳下警車,衝進街心,交通早已停滯,人人都被檢查哨擋住了,他在車陣中穿梭,眼角瞥見車裡的人,男的躲在方向盤下,一輛休旅車中的婦人手忙腳亂解開女兒的安全椅。直到現在,在街心狂奔,他才想到他成了活靶子。
布洛迪把身體壓低。
距小巷還有一條街,他在靜止的汽車之間疾衝,跳上人行道,立刻背貼著牆,掏出手槍,雙手握住。他的動作很快,眼睛緊盯著巷子口,脈搏狂跳,儘管警笛和直升機的噪音很吵,他仍能聽見自己的喘息聲。三十步,二十,十步。
布洛迪接連吐了兩口氣,彎過轉角,葛拉克手槍在前。巷子是典型的芝加哥小巷,電話柱,甜膩的垃圾味,路面坑坑巴巴的。一個人影也沒有。三個垃圾箱,兩個加鎖。
第三個的鐵鍊丟在地上,蓋子掀開了。
布洛迪察看了近傍晚的陽光角度,側步而行,以免影子洩漏了他的形跡。悄悄前進,舉高手槍,手指貼著扳機。垃圾箱越來越近在眼前。垃圾被推到一邊,讓出了一個足可讓一個男人跪下的空間。生鏽的金屬壁腳有一堆彈射出的銅彈殼。
彈殼中還有半根香菸,並未捻熄。
一縷煙升起,扭轉,只一瞬就消失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