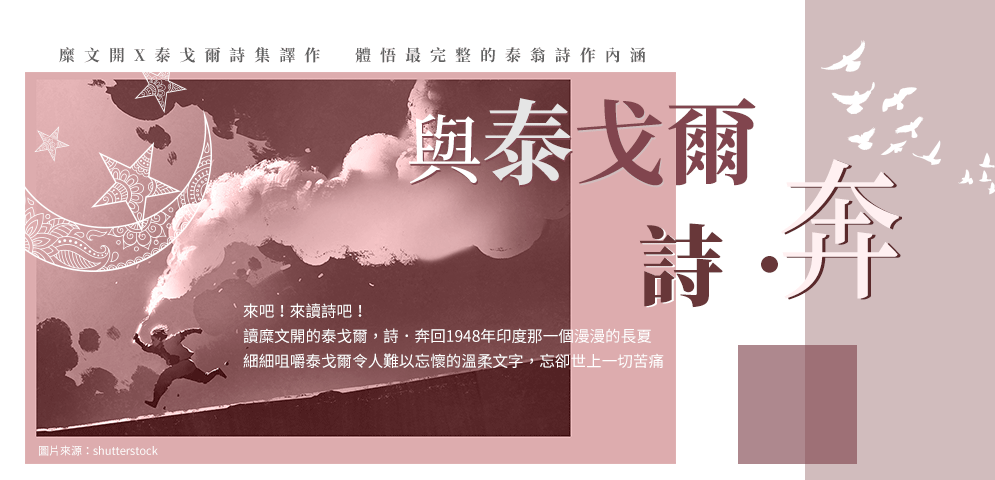 |
|||||||
|
|||||||
|
● 泰戈爾在臺灣的代言人:糜文開 印度,有點熟悉又遙遠神祕的國度。古遠的天竺故事和印度歌舞人人皆有印象,但印度現代的歷史和文學卻又似乎相當陌生。泰戈爾可能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現代印度作家了:身為亞洲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泰戈爾在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名聲響亮,不但曾親訪中國,與徐志摩、林徽因的交往讓人津津樂道,梁啟超也為他取了個中文名字「竺震旦」。鄭振鐸在1922年譯出了他的《飛鳥集》,更是傳頌一時。 但在戰後的臺灣,五四詩人已遠,《飛鳥集》因鄭振鐸「附匪」而名列禁書書單,泰戈爾的名聲仍得以維持不墜,必須歸功於糜文開。臺灣市面上雖能見到鄭振鐸的《飛鳥集》,例如江南、輔新、漢風等出版社的版本,但都不署譯者名字,且書名一律都改為《漂鳥集》,也是因為糜文開的緣故。至今兩岸新譯本不絕,但無論譯者是誰,中國至今仍以《飛鳥集》為主流,臺灣還是繼續稱為《漂鳥集》,兩岸各有定譯,也是頗為有趣的現象。 糜文開(1908-1983)是江蘇無錫人,中華民國外交官,1940年代長駐印度,也在印度國際大學哲學系進修,與印度淵源甚深。1948年,他在印度大使館長夏無事,和同事容寶琛兩人偶然發現鄭振鐸的《飛鳥集》不全,且誤譯處不少,於是重譯此書,改書名為《漂鳥集》,理由是「漂鳥」比「飛鳥」更符合印度崇尚雲遊漂泊修行者的意象。序中說當初翻譯此詩集純為「消夏」,初無出版之計畫,他比較急於出版的是1948年上半年已經譯完的《奈都夫人詩全集》。為了這本詩集,他不但跟作者奈都夫人合照,夫人也寫了幾句給中文讀者的話,又請了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寫序,一切準備妥當,寄去上海商務準備出版。誰知1949年時局大亂,上海商務說無法出版了,糜文開羈留香港,只好自己開起出版社來。出版社叫做「印度研究社」,專出糜文開和女兒糜榴麗兩人譯作。原本計畫出五本書,第五本即《泰戈爾詩總集》,包含已譯完的《漂鳥集》和《新月集》,不過後來只出了前四種,《泰戈爾詩總集》並未在香港出版。 糜文開1953年來到臺灣,繼續外交官生涯,也在大學教印度文學。1955年,應朋友要求,在香港大學《生活月刊》連載早已譯出的《漂鳥集》,許多讀者為之驚豔,三民書局遂在1956年出版《漂鳥集》單行本。此後「漂鳥」成為臺灣的定譯,儘管臺灣還有周策縱在美國譯的《失群的鳥》和羅青的《單飛的鳥》,但都無法取代《漂鳥集》在讀者心中的地位。糜文開與糜榴麗父女合譯的《新月集》也繼《漂鳥集》後出版。糜文開又陸續與夫人裴溥言合譯其他五冊泰戈爾詩集,1958年出齊七冊。此時距離他在新德里消夏時翻譯《漂鳥集》已有十年,他自己漂泊港臺,歷經喪偶與新婚,境遇憂喜交織,恍若隔世,也見證了戰後文人流離遷徙的動亂時光。 《漂鳥集》和《新月集》風格完全不同。《漂鳥集》是精緻玲瓏的浮光掠影,短短一兩句人生哲理沁人心脾,的確足以「消夏」;《新月集》卻是童趣十足,親子情深之作,幾首敘事詩有情有景,難以忘懷。每一本譯作都與譯者的生命歷程交織而成,今天重看糜文開翻譯的泰戈爾詩作,似乎還能感受到1948年印度的那一個漫漫長夏呢! 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 賴慈芸 二〇一八年三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