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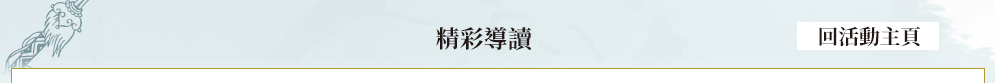 |
|||
|
天命所歸的悲情傳奇 南山 作為中國俠義小說的源頭,也是章回首部曲,《水滸傳》一直是目光焦點:「四大奇書」之首,「六大才子書」的小說界代表;也是眾矢之的:大山寨的荒謬締造,抗爭的蒼涼傳奇,淑世的悲情幻滅,「逼上梁山」的自我嘲弄……乃至於,當「聚義廳」改頭換面,掛上「忠義堂」的牌匾,「俠義」一詞,竟而淪為「敢笑黃巢不丈夫」最狹義的注解。 也就難逃歷來論者吁嘆、扼腕、激昂陳詞和點指攻伐。 可惜,明、清時期的科舉主考官,沒能突發奇想,出一道讓滿朝文武譁然、全國考生傻眼的申論題:你,飽讀詩書、胸懷天下、國之棟梁的你,對「秀才造反」有何看法? 或者:如果你是宋江,在完成大聚義,天罡地煞強勢回歸之際,會如何決定梁山的未來攻略? 好一記又快又猛回馬槍,反刺數千年來由儒家文化棉花糖層層包覆的政權更迭、忠義迷思。 所以,這部堪稱「強盜完全實用指南」、「造反懶人包」的血腥鉅作曾被列為禁書。 很難回答?哈!你可以大筆一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這位秀才又以「君子」自居,那恐怕要等更久。為什麼?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怒」的氣體分子結構 以現代觀點回看那齣君權時代的草莽故事,深具民主或民粹素養的你我,恐怕不大容易釐清這部「怒書」(張潮語)的氣體分子結構:憤世書生的酸氣?不平世道的鳥氣?暗昧時局的濁氣?群魔亂舞的鬼氣?占山為王的神氣?昏君奸臣的沆瀣一氣?歷史鍋爐熊熊的火氣?黎民蒼生的怒氣? 說到重點了。那把「反貪腐」的大刀,劈開「忠良/邪惡」、「冤侮/賊佞」,像摩西分海,讓人赫見黑白二分,卻解不開梁山好漢(以宋江為馬首)一念之執打造的自我困鎖:忠君,就是順天承運。 看《三國》或《水滸》掉淚,是在為古人擔憂?換個輕鬆讀法,那些刀來劍往、攻城掠地,所謂「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縲線之厄」、「逼上梁山」(嚴格說,應是「殊途同歸上梁山」,真正的苦主只有林沖一人),場面浩大,特效驚人,但在本質上,純屬宣洩:儒家堡壘的廢氣排放,禮教文化的戲劇鬆綁,「替天行道」的一詞多解,以及,神話、邪說的誓必兩立。 神話?是啊!民族的集體潛意識,歷史的回聲;先民口耳相傳,也是古典小說慣用的仙神氛圍、敘事結構。一如女媧補天之於《紅樓夢》,《封神演義》之於商、周對抗;而《水滸傳》原著的開場,比現今任何一部奇幻電影更魔幻:一道從地穴竄出、「掀塌了半個殿角」的黑氣(黑色乾冰?)釋放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從此造亂天下。這種戴上反派面具的正派出場,教人不免懷疑:那是汙染塵世的PM2.5?讓整個積弱時代恢復電力的乾淨煤? 梁山好漢的軍事化行動,有一個很好用、合理化的藉口:替天行道。問題是,那個「天」,是指天意?天命?還是昏庸無能的天子?他們的「行道」邏輯:以牙還牙(誰動我兄弟,我就殺他全家;誰碰我全家,我就滅他全城),以毒攻毒(你黑心,我就吃你的心);以暴制暴(你有千軍萬馬,我有高手猛將),以亂易亂(你欺凌百姓,我禍亂天下)。繼而,以含恨替代冤屈(反奸佞終究被奸佞所害),以殺——卻止不了殺: 「三打祝家莊」殺聲震天,「大破高唐州」哀鴻遍野,「攻陷青州城」死傷慘重,「擊潰大名府」血流漂櫓,「擒王慶」、「滅田虎」、「討方臘」更是屍堆成山——至此,刀戟沉沙,鳥盡弓藏,一百零八條好漢只剩下三十六人,慘勝而歸,等著完成悲壯大結局:童貫、高俅等朝中奸臣,為盧俊義、宋江和李逵費心張羅的毒殺戲碼。 回顧血淚一生,梁山好漢或許明白一件事:逆勢行道不如返鄉,當一株靜觀時勢流變的行道樹。至少,可以行光合作用,化消少許烏煙,吸收若干瘴氣,也算是功德一樁。宋江死後,吳用和花榮在其墓前大哭一場,自縊而亡——沒有樹行嗎?不妨視為抗爭尾聲最寂靜也最極致的抗議,無言的向天詰問,穿時越空的訴願。 神的視野‧四維觀點 若是以神的視野俯瞰哀哀人寰,那些興衰治亂、物換星移、新紀降臨乃至世界末日,不過是一盞熱茗的隱隱浮煙?萬里黃沙的一瀑塵暴?或者,一壺濁酒,神與魔,喜相逢? 而在天、人之間,你我高談闊論,饒舌辯證,猶能換轉「觀」點,分說管見: 宏觀:數千年中國歷史,不就是一部血跡斑斑殺戮史?《水滸傳》、《三國演義》是打殺鬥爭濃縮版;漫漫長河中,難得幾回太平盛世,是神的恩寵?無垠荒漠的海市蜃樓? 微觀:梁山好漢的個別際遇,是人類齒輪的連鎖錯動。他們或者身負不平,或者路見不平;在萬能的神啟動「路平專案」前,他們但憑一己之力,打不平或抱不平,具體而微表現出古往今來現實人間的血腥本質:殺伐,迫害,凌辱,暴虐…… 客觀:歷史永遠是對的,她說什麼就是什麼。人類史上任何一齣善惡有報或天地不仁,都是真理。她比所有口號、教條、信仰……九流十家的聖言或邪說,更能表現天意。 主觀:既是天意,天最大,誰能逆天?於是,「負嵎頑抗」是姿態?還是選擇?後者代表九死不悔的勇氣,前者呢?可就暗藏驚天撼地、感動鬼神的智慧了。 昏茫世道,該當如何?我們重人道,守天道,卻挖不出脫出困境、通達八方的地道。 改寫的藝術 以上所述,非關筆者淺見,而是新新古典《水滸傳》作者張啟疆循字沿句、埋設鋪陳的現代見解、多維史觀。 閱讀,是一門學問:博覽,精讀,思辨,領會,吸收,化用,端賴讀者的胸襟識見。 改寫,是一項藝術,也是異數:不論你是快手、慢手、代工高手、紅油抄手或無所不能的寫手,切記:你的生花妙筆,是在雜花生樹的森林裡,栽育奇葩。何處接枝?哪裡移植?文字、腔調、形式、結構都得翻新,同時要保住原著的精神與精髓。創意、「古意」並存,讓讀者在老戲碼裡看到新戲法,有所本,卻也無所泊靠:改寫者若不能提出自己的見解,或者說,史觀——不論是對那段歷史,或原著中暗藏的歷史批判,再怎麼長篇累牘、洋洋灑灑,只能稱為:依樣畫葫蘆、鸚鵡式仿說。 虛實交映 從某種角度看,所謂「改寫」,其實是「再創作」。 小說家族不全然是向壁虛構,也不會是單純的現實模擬、史實記寫;或者說,虛構文本不代表毫無根據,取材現實不等於「忠實反映」——創作之妙,就在虛實交錯,相映成趣。 有些作品乍看天馬行空,細究之下,處處可見現實的投影。有些文本現實感十足,讀者按章對號,以為是「純屬真實」之作;殊不知,那是作者神遊「日用常行」,化轉素材的功力展現,或者,借喻寄寓的曲筆用心。 今是昨非、借古諷今,都是此一手法的委婉表現。 簡言之,小說書寫,是在真幻兩端進出折返的虛實辯證。 而脫胎自歷史(實),或者說,若干情節符合史實的章回、戲曲(虛),更容易看出兩者間的比例和錯動。 如《三國演義》之於《三國志》,加油添醋的枝節不少:草船借箭、孔明借東風、空城計等等。 《水滸傳》之於《大宋宣和遺事》之於北宋史,更是大張旗鼓,擴增規模,將一場地方造亂,弄成神、人共憤的中原大戰,很像古裝版《復仇者聯盟》;不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全員參戰,九天玄女也來湊一腳:賜三杯仙酒,贈三卷天書,引領天魁星宋江率眾歸位——一齣早譜寫好的劇本史話。 新新古典《水滸傳》之於《水滸傳》呢?張啟疆的現代文本,如何虛裡構虛、巧轉虛實,也就是前述帶著雙重虛構性質的「再創作」? 串帶式出場 先看結構: 《水滸傳》人物眾多,情節博雜,如何安排戲分、決定順序、排名先後,頗為「耐」人尋味。 瞧!施耐庵先生用了一手不慌不忙的「聯合主演」方式:串帶式出場,大手牽小手,一個帶一個。每一名登場人物,除了交代自身故事,還得負責承先啟後,接棒交棒,讓各自遭遇串連成線,續接如流,合成轟沸亂世的怒潮飛瀑、集體命運。 鑲嵌式結構 以「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為楔,該書的神話底蘊不揭而露。只是,第一男主角(非指重要性,而是出場序)竟是「浮浪破落戶子弟」高俅,對照故事尾聲的英雄末路、小人得意,實在有些殺風景——也許,作者就是要讓讀者恨得牙癢癢。 張啟疆的「新水滸」,分為上、下兩部,用到和原著迥然不同的形式:鑲嵌式結構,對映性敘事。也就是打造虛、實兩座舞臺,以雙軸分說、時分時合的技法,呈現對照效果、戲劇張力。 有趣的是,上部和下部各有虛界與實境;交纏的指涉、映現的內容,亦大異其趣。 上部採「說書式開場」。也就是「卷首語」:「時窮年荒,赤陸千里」的時代,「朔風吹得正緊,飛雪如絮」的河畔小徑,一間「斜插屋簷、汙漬斑斑酒旗」的茅店,聚集了書生、武者、商賈、拿刀執鞭的江湖人士……你高談,我闊論,七嘴鬥八舌;經由英雄傳說,開啟了「伏魔大殿誤放了早年洞玄真人鎮鎖的一百單八個魔君」的楔引,也預告一齣山雨欲來的江湖風波、政治風暴。 藉由人言包裹神話的「加框」,讓故事穿上故事外衣,也教故事暗藏故事內裡。而在論豪傑、斷魔君的舌劍脣槍中,帶出第一號英雄:「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身長八尺,使得一手好鎗法」的林沖。 也就是第一章「林沖夜奔」的內容。 實空‧虛影 乍看之下,客棧(茅店)為實,店裡發生的議論,以及後來的高潮反轉,為小說實空:真實的時空舞臺,卷首語、卷中語和卷末語,貫穿敘事主軸。相對地,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正文部分,反而淪為各說各話的虛影——林沖、魯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人的事跡,乃是客棧中人說唱擬仿的傳說人物。 真是這樣? 兩者並非涇渭分明的主(實)客(虛)體,也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平行線。隨著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故事)推展,天地線漸漸傾斜,「實空」、「虛影」變得時遠時近,彼此拉距,互相干擾。第四章「七星聚義」赫見虛中有實:正文中突然插進「卷中語四」,和前後文形成微妙的共振與互補,章末又見「卷中語五」,自成一脈,且呼應著第五章「黑旋風李逵」裡「黑猩猩」打、殺、火、罵加上法場劫囚的轟鬧演出——套用中年文士(梁山要角所扮)的話:「……只是大圖景裡的小拼圖。」 鑲拼、環扣、翻轉、輻輳……合成天書符籙中祕而不宣的讖景。 到了第六章「大宋王朝的江山」,虛實交錯渾似亂針刺繡:山雨欲來的卷中語七、八、九、十,接連跳進兵荒馬亂、駭浪驚濤的正文敘述:宋江殺惜、亡命天涯、再陷囹圄、人肉包子店、法場問斬、殺出重圍……直至上部「青幡白旌;黃鉞皂蓋,緋纓黑纛。山頂一面杏黃大旗,書著『替天行道』血紅大字」的收尾:宋江上梁山。 與此同時——是的,當下時空和過往傳聞愈來愈貼近,終至疊合——客棧裡爾虞我詐的議譚,也到了「卷末」高潮:故事和故事裡的故事共舞,你的張良計,單挑我的過牆梯;最驚險的暗樁,出自最意想不到的敵人。一場惡戰——殺宋、保宋人馬大火併——猝然發動,瞬間結束,徒留重重疑雲:「雲層深處忽忽閃現龍章鳳篆蝌蚪之書」,射人眼目,難以辨識。 梁山諸將的運命,從此踏進地雷區。而外來勢力(此為原著所缺的謎讔,筆者暫不戳破)的入侵,竟是江山爭奪戰的預演;梁山軍師吳用,林沖、武松、王進等「傳說人物」,早已入局,埋伏客棧,智破對手毒計,確保公明回歸,以及,「說唱擬仿」自己的來時路。 真、夢對照 上部如此交纏,下部呢?下部為例?不!張啟疆變出新招:以夢境替換茅店,穿時越空的集體夢識,倒映現實慘烈、前景荒涼。 何謂「倒映」?吉凶倒反,死生易位,成敗相隨,禍福難料卻可觀:像燒盡九重天的大火,烘亮昏茫的未來時空。 藉由「驚夢」之一到之九,反寫迢迢征途的荒謬突梯。這九齣夢,分屬宋江、李逵、戴宗、吳用、柴進、林沖、公孫勝、魯智深、武松等人,連已陣亡的「托塔天王」晁蓋,都還魂登場,敲一段「雙龍搶珠」、「天命所歸」——簡單說,替宋江背書——邊鼓。夢相徵引,夢劇續連,既是私魘,也算共業,小我之夢合為九夢連環(其中,驚夢六又一分為二,驚夢一和九,首尾呼應,夢主都是既想行天道又盼封侯爵的宋江)。他們夢見什麼?堂皇出征前的預示(視):不是眼前的輝煌戰果,而是遙遠未來的災禍。一挫一揚,一喜一悲,他們該相信何者?現實?夢境? 以第六章的驚夢六之二為例,公孫勝在夢中「預見」:宋江上前,跪伏奏道:「臣等奉旨,平定淮西,將王慶獻俘闕下,候旨定奪。」顯然已到「擒王慶」的階段。真實時空呢?仍在「大破高唐州」前後。 換個角度看,真實與夢域,如前所述,「相映成趣」,也成謎。想像一種詭異至極的場景:梁山好漢齊聚一堂,觀賞歷史大銀幕上最不可思議的分割畫面:現在、未來分據兩側,禍福因果同步完成;中間那道楚河漢界,是牢不可破卻也杳不可尋的時光虛線。 數字玄機 再者,下部的章節排序,有著明顯的數字玄機:第一章九天玄女、第二章八虎會梁山、第三章七星再聚……第七章三山歸附、第八章(上)二龍搶珠(下)二把交椅、第九章一字成書;一至九,九到一,反向而行,有如逆錯的天機與數讔。從「九天玄女」一路倒數,直至「一字成書」,又像是歸零的卷帙、「千算萬算不如天一劃」的奧義。 如果說上部的主題是宋江歸位,締造大聚義;顯然,下部的主調,乃為眾星殞落,完成大演義:一場至死方休的無限之戰。三打祝家莊,大破高唐州,攻陷青州城,擊潰大名府……童貫、高俅傾全國之力組成的水陸大軍,也慘敗於這一批精兵良將。朝廷迫於梁山之強,強可敵國,只好派人招安。 打。打不完的戰爭,殺不盡的敵人。和朝廷、官府、地方惡霸、敵對山寨打;歸順之後,又被派去攻打「四大寇」(宋江為其一)的其他三人: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這有點像,今日我討伐昨日我,曾經反抗貪腐昏庸的,如今站在昏庸貪腐的一方。哪個我,才是真正的我?於是,更慘烈的「自我戰爭」遍地竄燒:「義」與「忠」的激辯、鷹派(主戰)和鴿派(主和,其實是降)的矛盾,乃至於,拋灑熱血,豁拚性命,對抗神諭、預言、夢識、反覆世局、不測人心……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盤據歷史天秤兩端;古有七傷拳,傷敵七分,自損三分。宋江式猶疑瞻顧的「造反」,注定留下斑斑血痕:親人慟傷、世人悲傷、史家感傷、智者神傷、弱者憐傷、勇者挫傷,而後人或讀者,掩卷之餘,心中泛起無由哀傷? 三杯仙酒,釀化萬般滋味;三卷天書,合成三字包袱:忠,君,報……報什麼呢?報國?報仇?報復? 讀《三國》掉淚,是在為古人擔憂;觀《水滸》憂心,是在為今人掉淚。昏亂世道,同樣擁有選擇權的你我,該當如何?這一題,看似輕易可解,卻足以教新新古典《水滸傳》的作者、撰寫本文的筆者、句句拍案字字驚心的讀者你……都陷入比圍棋長考、赴京趕考更遙迢的魔考。 戊戌年仲夏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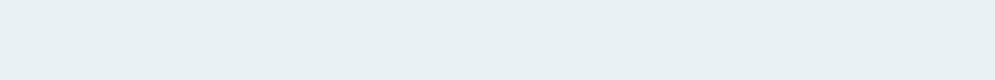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