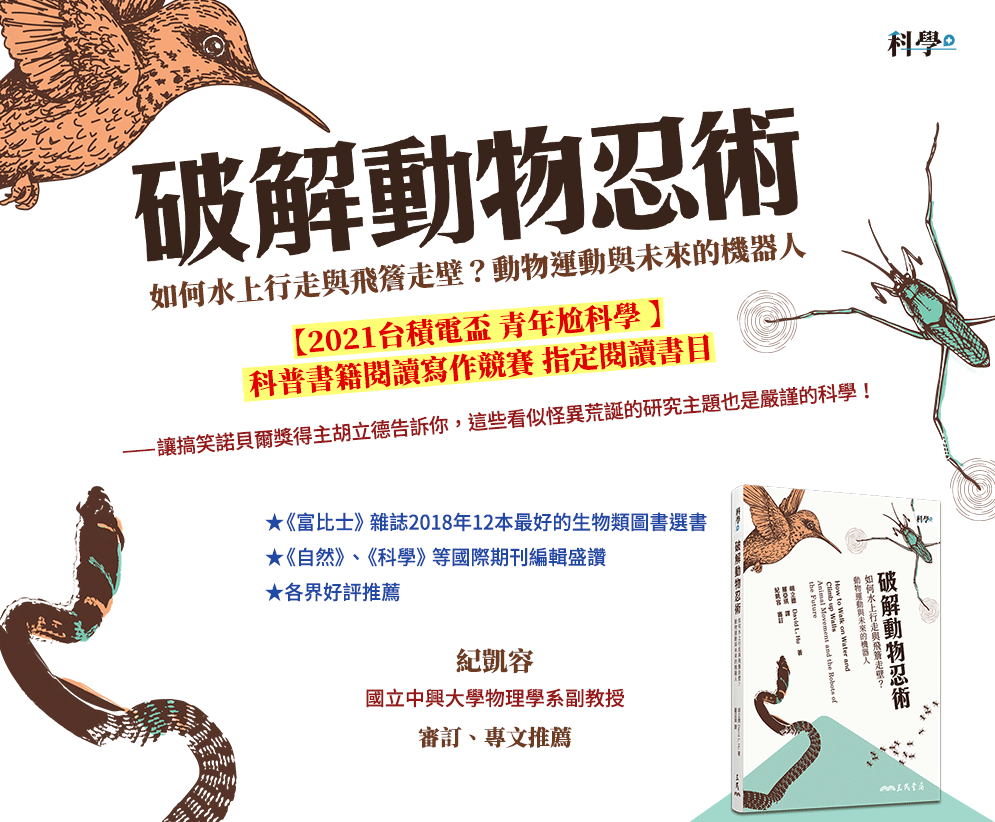 |
|||
|
|||
|
動物運動的世界 我頭一次遇見我太太時,她帶著一隻名叫傑瑞的咖啡色玩具貴賓犬。那是她前男友送她的情人節禮物,也正是我下一個科學實驗的完美受試者。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傑瑞的身上黏便利貼,接著用高速攝影機拍攝牠。傑瑞不怎麼喜歡這些便利貼,一直想把它們咬掉,如果便利貼黏在牠的頭頂或脖子上,牠還是有辦法可以弄掉。牠來回甩了幾次身體和頭部,讓我不禁倒退一步,牠的咖啡色捲毛飛了起來,連同那些便利貼一起,把塵土和跳蚤甩得到處都是。這個小招數稱作「狗兒甩」,乍看之下似乎是個沒什麼用處的蠢動作。 當我分析高速攝影機拍到的畫面時,發現傑瑞的狗兒甩所產生的加速度是地表重力加速度的12倍,比一級方程式賽車轉彎時的加速度還要大。我幫牠洗澡時,發現狗兒甩竟然可以把牠皮毛之間高達70%的水分甩掉,牠只需要不到1秒的時間就能做到的事,我們的洗衣機卻得花上數分鐘才能辦到。狗兒甩怎麼會這麼有效? 於是我的學生安卓‧狄克森 (Andrew Dickerson) 和我做了一個狗兒甩模擬器,那是一個會旋轉的柱體,將傑瑞的一撮毛以我們觀察到的速率進行旋轉。我們在這個旋轉架上設置了一臺攝影機,這樣就能看見狗毛旋轉時甩出的水滴,就好比我們坐在前排觀眾席上觀看水滴噴發的過程。利用狗兒甩模擬器,我們發現要移除狗毛上最小的水滴,加速度至少必須是地表重力加速度的12倍,正好和傑瑞所產生的加速度相符。 為了查明甩水能力是不是傑瑞特有的,我翻遍亞特蘭大,不只拜訪校園裡的實驗室、當地的公園,還去了亞特蘭大動物園,竭盡所能找到最多種類的動物。接下來的幾年,動物園漸漸習慣我所提出的一些怪異研究要求,例如:「我們能不能過來拍攝貓熊甩水的樣子?」最後,我們用高速攝影機拍到的動物之中,最小和最大的身體質量相差10,000倍,從老鼠到熊都有。熊每秒甩動身體4次,狗每秒4~7次,大鼠每秒18次,而小鼠則高達每秒29次。人類每眨一次眼,小鼠就能甩動身體10次以上。為什麼愈小的動物每秒甩動的次數愈多?因為體型較小的動物旋轉半徑較短,因此所產生的向心力較小,為了產生跟大型動物一樣的甩水力量,就必須轉動得更快。 傑瑞的主人給了我一輩子的愛和兩個完美的孩子—他們之後也不知不覺地成為我的實驗對象,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會告訴你更多我們一起經歷的冒險。然而這隻咖啡色的玩具貴賓犬傑瑞功不可沒,是牠讓我拿到入場券,進入動物運動的世界—這個令我著迷不已的科學領域。 不同的動物看起來或許很不一樣,但是牠們全都有一個共通點:必須動才能生存。「動」這件事之所以會演化出來,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對能量的需求,而這是區別動物和植物的其中一點,因為植物通常是固定不動的。植物屬於「自營生物」,因為它們可以利用陽光製造出自己的食物,對植物而言,除了繁衍後代時之外,大規模的移動是不必要的。相較之下,動物是「異營生物」,得不斷尋找食物來吃才能獲取能量,植食性動物為採食而移動,掠食者則是為了捕食而移動。掠食者也好,獵物也罷,能夠迅速移動並做出反應,就是讓自己不被吃掉的方法之一。然而,若動物耗費愈多能量來移動,就需要吃得愈多來作為能量補給,因此動物在速度、節能與機動性方面經常挑戰極限。 動物的移動也涉及到要如何在各種環境中穿梭。我們很容易就忘了應付自然環境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我們可以輕輕鬆鬆地搭乘飛機飛越各種環境,或者不加思索地開車開好幾百公里。相形之下,想想鴿子,牠從甲地飛到乙地途中,可能會在空中遭遇渦旋或其他亂流,將牠吹離原本的路徑。牠所飛越的空中充滿各種障礙,像本身也可能被風吹得來回搖晃的樹枝。你或許會以為這些困難只出現在空中,但地面上的動物其實也會遇到同樣艱困的難題。一隻從甲地前往乙地的蠑螈可能會在途中遇到樹枝、林地的枯枝落葉或是泥濘,為了把卵產在潮溼的環境,牠甚至可能需要從陸地轉換到水中。 不斷變動的世界會改變動物移動的條件,晝夜和季節的交替,都會使動物的移動方式跟著改變。動物必須面對下雨、雨夾雪和降雪等天氣型態。從春天開始,蜜蜂會採集花粉,從一朵花移動到下一朵花,過程中可能會完全被花粉沾裹。除了被無生命的東西所覆蓋,有時動物也必須面對和同種成員聚集在一起的狀況,想想看一群鴿子或魚簇擁的景況:牠們跟我們一樣,覓食的時候也會碰到交通阻塞。 從甲地移動到乙地雖然很重要,但還有另一種規模較小的移動類型,對生存來說也是同等重要。動物會將物質送進、送出身體,這是進食和產生廢物的關鍵動作。我們通常不會特別去想這些動作要如何進行,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興建完善的世界,有湯匙或鏟子等設計好的現成工具可以運送物質。在大自然裡,動物是用自己身體的某些部位來處理物質,比如狗兒用柔軟的舌頭舔水,大象用靈活的長鼻子拾取水果。動物活在一個充滿壁蝨和跳蚤等寄生蟲的世界,因此理毛這個動作可能會攸關生死,對付這些寄生蟲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動物的動作,這些動作通常運用身體部位來達成。以貓的舌頭為例,它就像一把梳子,但比梳子更強大,貓舌上布滿了大量的尖刺,刺的尖端有個U型凹穴能自動吸收唾液,在刺碰觸到個別毛髮時再將唾液釋出。 動物運動隨處可見,這是動物的首要處世之道,如此多樣的運動是如何產生的呢? 動物運動的多樣性因為同一件事而成為可能:演化。演化看似簡單,但其實是種很強大的演算法。生物會進行繁衍,複製出不完美的自己,也就是說,後代和父母長得不一樣。如果當中有些變異增進生物生存或繁衍的能力,而這些變異又可以傳遞給這些生物的後代,那麼該族群就會隨著時間演化並適應環境。這件事說起來簡單,但很少人能想像得到演化在這三十五億年來創造出多麼龐大的多樣性。 無論多麼怪異的動物運動,都是源自演化的過程。水上行走就是一個迷人的例子:昆蟲大約在四億年前演化出來;三億年後,陸上的昆蟲和蜘蛛開始占據水面,這次的遷徙幫助牠們躲避掠食者,以及找到新的食物來源和孵育後代的安全處所。現存最原始的水上行走昆蟲是水蝽屬 (Velia) 這個屬,長得很像牠們的祖先。牠們和許多陸生昆蟲一樣,如螞蟻般用六隻腳的腳尖行走,這個動作在水面上並不是很管用,牠們會瘋狂地動來動去,卻沒有什麼進展,好比一直在冰上打滑似的,此外,緩慢的步伐讓牠們的活動範圍限縮在靠近岸邊的地方。這些原始的水上行走昆蟲棲息在淺水處,浮萍和其他植物讓牠們有地方可以攀附,以保安全。 隨著時間過去,這些昆蟲的中足變得比較長,賦予牠們用腳尖行走的明顯優勢;最後,牠們的腳長到可以用來當作槳,這個新物種叫做水黽,能夠像船一樣划行,並把其他步足當作浮筒一樣用來平衡與支撐,這樣的步法 (gait) 非常有效,因此這種昆蟲幾乎不可能徒手抓到。但反過來說,水黽因為變得太專精於水面上移動,所以在陸地上反而移動得很緩慢,笨拙地把槳一般的腳拖在身後。水黽已經回不去了,水面已經成為牠們永久棲身之所。 演化出水上行走能力的,不只有無脊椎動物。綠雙冠蜥是一種帶有白斑和黃色大眼的綠色蜥蜴,牠移動起來跟一般蜥蜴無異,但是受到驚嚇時,可以在水面暴衝一下子,牠用長如流蘇的腳趾來拍打水面與支撐自己的重量。同樣地,黑白相間、有著紅眼睛的西鸊鷈也能在水面上奔跑,即便牠的體重是綠雙冠蜥的10倍。當雄西鸊鷈做出複雜的求偶動作「急衝」時,會跑過50公尺的水面,以吸引雌鳥,即使已經選好配偶,雄鳥和雌鳥仍會一起在水面上奔跑,來鞏固彼此的連結。綠雙冠蜥和西鸊鷈都受到各自演化起源的限制,雖然最小型的脊椎動物跟昆蟲一樣大,但綠雙冠蜥和西鸊鷈都因具有內骨骼,使牠們太大、太重,而無法像有著外骨骼的水黽一樣能毫不費力地在水面上行走。 人類也無法克服自己的演化起源:我們的腳太小,以至於無法在水面上撐起自己的重量。李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曾構思一種狀似獨木舟的浮板,用來穿在腳上,只要靠兩根尖端帶有浮標的竿子,人們就可以小心翼翼地在水上滑行。然而,即使有這樣的工具,我們也永遠不可能像綠雙冠蜥那樣在水上奔走,因為我們的肌肉無法產生足夠的功率,用夠快的速度推動水來支撐我們的體重。演化既是福,也是禍:它讓許多動物只擅長在特定的介質中運動,像是空氣、陸地或水裡。比方說,演化讓我們在陸地上行走時極為節能,但在水面上行走時卻相當彆扭;水黽則恰恰相反,牠們在水上很優雅,在陸地上卻很笨拙。 動物運動並不是新的研究領域,事實上,這至少已經有四百年的歷史了,早在我們有能夠仔細探究相關課題的儀器設備以前,人們就很好奇動物是如何向前推進了。最早開始探究這些問題的其中一人,便是偷偷解剖動物和人體的李奧納多‧達文西。達文西在素描簿上不只畫了鑽床和直升機,也畫了很多動物的解剖圖,彷彿動物也是機器。當時,有許多人相信「生機論」(vitalism),也就是生命體都有靈魂,雖然從來沒有人成功觀察或測量到靈魂,但這就是讓生物有生命的原因。不過達文西不相信這種神祕的觀點,而是運用邏輯看待世界,他認為周遭的一切無論多麼神祕,都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理解。 《生長與形態》(On Growth and Form) 一書讓數學家和非生物學家對動物運動產生興趣。此書在1915年寫成,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延後到1917年才出版。作者達西‧湯普森 (D'Arcy Thompson) 是一位蘇格蘭生物學家,同時也是數學生物學的先驅,他提出的論點是:生物學家一直都不夠強調力學與物理定律對生物形體和生長所造成的影響。他在書中用數學描述了魚類、鳥類和哺乳動物的形狀。此書並不完美,因為湯普森並未接受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天擇說,但它依然啟發了無數個世代的藝術家和科學家,讓他們開始跨學科,運用數學來描述動物的形狀。動物形態學出現了嶄新的樣貌,生物學家利用數學描述動物的形態,例如演化出長如狗魚和扁如比目魚等形狀迥異的魚類。描述這些形狀是了解動物運動的第一步,因為動物的形狀會大大地影響牠們在流體中移動時所感受到及產生出的力量。 生物學家持續運用力學,進而催生出「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這個以探究動物運動及形態背後的物理法則的新學科,而劍橋大學的動物學家詹姆斯‧格雷爵士 (Sir James Gray) 可說是現代生物力學之父。如今,生物力學已不像當時劃分得那麼明確,因為現在這個領域也和微觀尺度的細胞生物物理學和聚焦在人類的運動生理學等課題有所重疊了,但從本書的目的來看,動物的生物力學確實是由格雷開展的。在1930年代,格雷進行了最早一批有關魚類和海豚游泳的研究,當他計算海豚游泳所需的功率時,赫然發現海豚應該是無法游泳的。這個矛盾的現象後來被稱作「格雷悖論」 (Gray's Paradox),持續吸引非生物學家來研究動物的運動,例如數學家詹姆斯‧萊特希爾爵士 (Sir James Lighthill) 就對魚類如何藉由身體運動來迅速或節能地游泳十分有興趣。 新興科技讓我們可以拍攝出更清晰的動物圖像,活化了動物運動的研究。在1930年代,電機工程師哈羅德‧埃傑頓 (Harold Edgerton) 讓可捕捉高速運動的頻閃攝影 (strobe photography) 變得普及。數十年以來,電腦的商業化讓人們得以運用高速攝影機和電腦演算法來自動追蹤游魚及牠們身後的水流。到了數位時代,機器人學和3D列印等新興製造技術也有長足進展,後者是特別重要的工具,在動物運動科學家間愈來愈普遍。我們將會在第四章討論人造鯊魚鱗片時談到3D列印。 而今,學科領域間的逐漸整合是致使動物運動學研究往前邁進的重要關鍵。學習流體力學的學生熱衷於修習魚類解剖學課程;設計攀爬機器人的機器人學家會閱讀首先探究昆蟲如何抓住表面的德國生理學家的經典著作;材料科學家會將牡蠣殼等生物材料帶進實驗室,碾碎之後用顯微鏡檢視。多方顯示,其他領域的科學家愈來愈能接受生物學的技術與實務,也對生物學的興趣愈發濃厚,這些領域也反過來將新的概念構想與高科技儀器融入生物學研究中,創造出二十年前不可能會使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在我看來,這是動物運動研究的轉捩點。 本書的目標是要向讀者介紹動物運動的世界以及研究這個世界的科學家們,在書中我特別著重於科學家用什麼核心概念來理解動物運動的多樣性,好讓讀者知道,只要掌握幾個物理學概念,就能憑直覺來理解不少動物的形態與運動。我希望透過這本書讓人們明白,研究動物的運動可以為一些對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的難題提出解決辦法,例如設計出效能更好的螺旋槳,或是發明可以照顧年長者的機器人。 有關動物運動學的書大部分是根據動物居住的媒介(如空氣、水、陸地)來劃分的,也有一些書是以動物的運動方式進行分類,例如行走、跳躍、游泳或飛行。我並沒有採用這些區分方式,而是聚焦在運動所涉及的物理原理上,如此就能將看似迥然不同的動物歸成同一類,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鯊魚和睫毛一起放在第四章,因為兩者都跟會影響流體行為的緻密表面結構有關。當把焦點放在物理學原理上時,我也就能將動物和機器人擺在一起,因此我將步行機器人和游魚一起放在第五章,因為兩者都藉由能量轉換來減少推進所需要的能量,換句話說,就是兩者的燃料經濟或油耗里程數都很高。然而,在這本書中我會盡量避免使用「效率」一詞,因為從工程學家的觀點,只有在動物爬坡時,效率才不會為零,惟有此時,動物才為抵抗重力而作功,在平地上以固定的速度移動其實不需要作功,因此也就不能使用效率一詞。這些說法可能違背你的直覺,但我會在第五章用牛頓定律來說明。我認為把焦點放在原理而非表象上,有助我們以嶄新而有用的觀點來思考動物運動。 你將會發現,這本書非常著重流體力學,也就是探討空氣和水等流體如何運動的物理學。超過70%的地球表面是由水構成的,因此有很多的動物已經能適應在水中運動。此外,許多動物的身體是由70%的水所組成的,每天都必須攝取水分,所以動物體內也有各種運作機制來促進液體在體內流動。動物也會產生液體,像是用來潤溼食物的唾液或排出廢物的尿液,我們在第三章談到特定的身體或器官形狀如何有效地驅動液體流動時,就會討論到排尿。 我在安排本書架構時,也刻意在每一章放入幾位關鍵科學家的故事,我的目標是把科學發現的經歷當成推理故事來說。我在年輕時很喜歡看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的推理小說,因為我可以在她為每個案件鋪陳細節時,順著她的邏輯走。我也很喜歡那些讓每個案件生動起來的奇特角色,跟著這些科學家的故事走,我們也會遇到一些有意思的角色,有時這些角色可能是科學家所使用的機器,如風洞和高速攝影機,有時則是來自生物、工程和物理等不同領域的研究團隊成員。我雖力求展現科學發展背後所須具備的團隊合作,但為了說故事,往往會把聚光燈投射在主角身上。我特別選擇科學家在職涯早期所進行的研究,好讓你了解涉足新的研究領域是什麼樣子,我挑選的研究多是在2000年到2018年之間發表的,因此這些科學家當中仍有很多人還活躍於研究工作(但要看你是何時讀這本書的)。當然,關於動物運動的書若少了動物本身是不會完整的,這些角色有時不太配合,不會乖乖交出自己的祕密。 美國天文學家卡爾‧薩根 (Carl Sagan) 曾說:「科學是一種知識體系,但更是一種思考方式。」希望隨著這幾位科學家的旅程,我可以傳達出他們是如何解決動物運動的課題。這些科學家在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收錄在參考書目裡,但這些文章通常不會描述科學旅程的細節和找到新發現的那一刻。這方面的素材都是我在2015到2017年之間訪問這些科學家時所獲得的,也都經由科學家本人閱讀並確認過。對他們而言,科學過程包含幾個關鍵步驟。首先,他們構思希望檢驗的想法,再將這個想法形塑成一個定義明確的研究問題。接著,他們設計出能解答這個問題的實驗,可能的話,會建造一個能測試原創概念的裝置。要取得進展,必須結合邏輯思考、團隊成員的協助、勤奮努力以及機緣巧合。他們的成功有多少是靠運氣呢?答案是:比你以為的還要少。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曾說:「在科學觀察的領域裡,機會只留給準備好的人。」我在述說發現的那一刻時會盡量放慢腳步,以便讓你看清科學家在驚呼「啊哈!」之前的邏輯步驟。發現的當下並非天才式的靈光乍現,不過是一系列有邏輯的步驟所帶出的結果而已。 在本書,以及動物運動學領域中,我們會脫離現代的生物學,因為它關注的焦點在細胞與分子層級,以及酵母、果蠅和老鼠等模式生物。人們會利用這些動物,是因為我們對牠們的了解夠多,可以進行嚴密控制的研究,反之,本書提到的那些科學家研究動物則是為了相反的理由――因為我們對牠們所知甚少。像飛蛇一定要在新加坡的雨林才能捕捉到,而不起眼的蟑螂得像寵物一樣養在實驗室裡才行。不管你覺得牠們神祕莫測還是令人作嘔,這些動物都能揭示物理原理,讓我們更了解「運動」――不只是動物的運動,也包含機器人的運動。 機器人的英文來自"robota"這個字,在捷克語中意為「被迫勞動者」,是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 (Karel Čapek) 在1920年發明的詞彙。自從進入電腦時代,機器人學這個領域便快速成長,機器人的工作場合也不再侷限於工廠。自動化技術在高低不平的地形上實行起來特別困難,而這樣的地貌在我們的星球上隨處可見,就連在一般住家室內也充滿各種不同的地形,像是地毯、硬木地板、成堆的衣服和小孩子的玩具。這些地方太難預測,充滿太多障礙物,以致輪子無法順利通行,所以有些人認為足式機器人可能擁有最好的移動方式,而若要替機器人設計腳,研究動物將會有莫大的用處。 研究動物也能讓我們明白體型大小的重要性,進而影響我們設計機器的方式。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體型大小會造成差異,當動物隨著時間成長,某些原本微不足道的力開始變得重要,比方說,大型動物無法承受跌倒的風險,因為牠們很容易就會跌傷。但若動物的體型愈小,由於尺度(scaling)大小所造成的物理效應,牠們的骨骼相對起來更顯強壯,這就是為何跳蚤即便跳到其體長120倍的高度,也不會受傷的緣故。體型小所帶來的無敵能力讓小動物得以做出更變化多端的行為,牠們天生較結實,因此即使常常撞到也不會受傷。這些與動物運動相關的基本議題也適用於機器,若能了解不同體型的動物在運動時有何差異,我們就能直覺地了解如何設計出不同大小的機器。 在這本書中,我會先從自己研究動物運動的開端談起,也就是我博士論文研究所探討的課題—「昆蟲如何在水面上行走」。對本書來說,這個主題應該是個不錯的起點,因為這類昆蟲相當常見,牠們總是悠哉地站立在池塘、湖泊和溪流的水面上,我們平常不覺得牠們有什麼特別的,但牠們顯然是大自然的傑作之一。為了了解水黽,我學會使用高速攝影機,這個工具對研究動物運動非常重要,因為可以捕捉到那些速度快到人眼看不見的動作。我會介紹表面張力的概念,這是流體表面會趨於減小表面積的趨勢,可用以解釋水為什麼會形成水滴狀以及昆蟲在水面上行走時如何支撐自己的重量。我也會介紹表面結構的概念,來說明水黽腳上覆蓋的細毛使其得以防水的原因。在認識這些昆蟲的旅途中,我認識了一位天賦異稟的機械工程學家,他製作出一隻機器水黽。第一章為本書的其他章節鋪好了路,它先從一個關於動物運動的簡單問題開始,最後以概念驗證作結,這裡的概念驗證指的就是建造一個可在水上行走的裝置。此外,第一章也展現了動物運動學領域非常歡迎沒受過生物學訓練的人加入。 第二章是從我完成博士論文之後開始說起,當時我到紐約進行幾年的博士後研究工作,探討的是蛇的運動。我從中學到,固體表面之間會以意料之外的方式互動,正因這種摩擦互動,蛇才有辦法毫不費力地在地毯或其他看似均質的表面上滑行,還有一些動物可以在沙粒和土壤間滑動,好似在水中游泳般。我把這一章放在水上行走的章節之後,因為在土壤中滑動就跟在水面上行走一樣令人驚嘆。我們光要在土壤中挖幾公尺深的洞,就得花上好幾個小時,但是擁有細長、流線身形的動物卻能輕易地潛入沙土。在這一章裡,我們也會學到另一種工具――可以拍攝地底動物的X光高速錄影機。 第二章會介紹到的其中一個重要概念是「最佳性」,也就是特定身形很適合在特定的介質中移動,例如,流線型的身體有助於動物在沙粒和泥巴中移動。第三章將更深入探討最佳性,我們會討論到三種動物,牠們擁有實現某功能的最佳身形。當然,演化的過程並非目標導向,而動物也因諸多限制而無法達到完美,因此,演化達到的是所謂的「全域最佳解」(global optimum)。然而,在我提出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動物十分擅長運用手上的牌。 在我們把鏡頭拉遠看過動物的整個形體之後,讓我們在第四章中將鏡頭拉近,來看看微小的世界。我們不太習慣觀看大型物體上的微小特徵,比方說,我們知道汽車的形狀,但我們有多常用放大鏡檢視汽車的表面?大自然和人造世界的差異就在這裡,動物是經由個別細胞增生而成長的,這個過程不只塑造出動物的整體形狀,也造就其體表的精細構造—細胞的生長讓鯊魚的體表長出細緻的鱗片,也讓你長出睫毛來保護眼睛。我會在這一章裡分別討論這些精密結構的流體動力特性。 動物運動的演化驅動力之一,是盡量以最高的燃料經濟性來移動,以節省能量供其他活動使用。另一方面,逃脫所採取的策略就不一樣了,此時速度最重要,例如水黽會迅速划行逃離,而魚在受到驚嚇時,則會展開C形啟動脫逃模式,亦即將身體彎曲成C形,然後像抽鞭子般快速彈動而游開。這類諸如衝刺的身體動作涉及很大的加速度,會迅速將流體運動轉換成熱。然而,節能對任何必須長途跋涉的動物來說都很重要,我會在第五章討論到使用極少能量就能移動的動物,並介紹「能量轉換」的概念,而這正是動物運動時得以節能的主要方式。 當我們走路時也會進行能量轉換:我們的腿就像單擺一樣,能將重力位能轉換成動能。魚類則將這個概念發揮到極致,牠們能從周圍環境中獲取能量,就像風箏會利用風力來移動一樣。 目前為止,我們尚未談到動物如何和障礙物以及環境中的其他不利條件進行互動。在人造世界裡,我們會盡量移除身旁的各種阻礙以利運輸,比方說高速公路就被設計得又平又直。相較之下,當蜜蜂飛過田野採集花粉時,會被數以千計且隨風搖曳的植物莖桿給圍繞著,牠們的解決之道令人難以置信,就是在尋找花粉途中一再地撞擊莖桿。蜜蜂的翅膀上有一個特殊的緩衝區,會像彈簧一樣儲存彈性位能,使其彎折時不致斷裂,我們在第六章也會談到昆蟲的其他防傷策略,像是蚊子如何安然度過暴風雨。 介紹到這裡,我只聚焦在看得見的動物適應,但在第七章,我們將談談看不見的東西――神經系統。昆蟲的飛行方式對神經系統是一大考驗,其中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就是在空中保持不動,也就是懸停。果蠅要在空中懸停很難,因為牠們的身體天生就不穩定,當牠掉落時,就跟一張紙一樣,不太會筆直落下,因為牠們會被自己墜落時所產生的氣流給影響。神經系統會跟身體一起合作,將懸停或其他運動類型設定為自動控制,自動化能讓動物無須太多指令,就能具有可重複且穩定的運動,就像開車時啟動定速巡航一樣。 到這裡為止,我們談的都是個別動物的運動方式,這在討論獨居動物時就足夠了,但還有很多動物是群居的,這將是第八章的討論對象。成群的椋鳥、野狼和螞蟻都是會合作的動物,合作是動物演化的關鍵創新,因為如此有利,所以一旦在某種動物中演化出來,就不會消失。我們會在這一章討論火蟻的互助合作以及1,000個機器人合作背後的工程學。 在本書的最後,我提出一些關於動物運動學未來發展的想法。我們正處在一個令人興奮的時期,無論動物運動學或相關領域的變化都正快速發生。而今,動物的身體和骨骼位置都可以用3D技術捕捉;科技讓機器人開始能做出栩栩如生的動作,而且體型也跟動物差不多;微製程技術讓昆蟲大小的微飛行機器人成為可能;仿蛇機器人被運用在搜救行動中;一種稱作生物混合機器人 (biohybrids)的新型機器人雖然是由真正的老鼠肌肉組織所構成,但形狀卻長得完全不像老鼠,而像是鬼蝠魟。有這麼多令人振奮的進展正在發生中,我將在這個章節提出幾件你也可以做得到的簡單事物,讓你參與這場發現之旅,幫助他人更加了解並欣賞領會動物運動這個研究領域。 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樣,很興奮地鳥瞰動物運動的世界。撰寫這本書的每個章節主題改變了我,還有很多同事。德國科學家海柯‧瓦勒利 (Haike Vallery) 曾經跟我說,她開始研究走路這件事之後,自己走路的速度也慢了下來,並仔細思索跨出的每一步。我希望當你閱讀每一章節時,你思考世界的方式也能發生改變。請記住,科學無關乎獲得解答,而是小心謹慎的探知,是對世界運作方式所產生的好奇心。當你開始探索動物運動的廣大世界時,請帶著這份好奇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