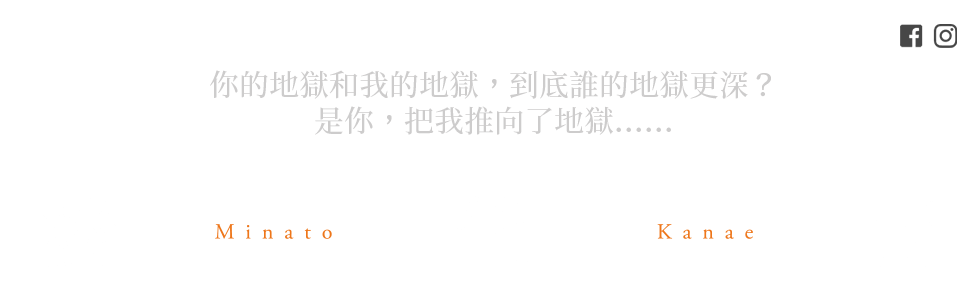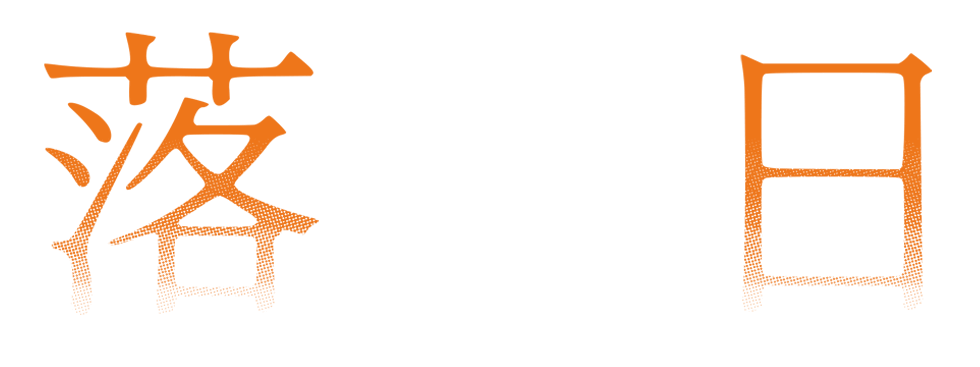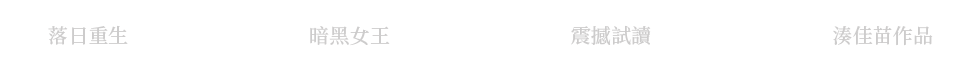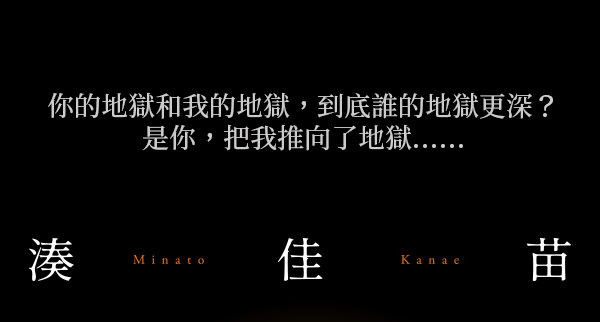【暮色珍藏版】
定價:450 元
特價:
90 折
405 元
放入購物車

哭是為了向他人求救,
如果無法指望有人來救自己,
會連哭的力氣也奪走嗎?
長谷部香怎麼也無法忘記那個飄雪的冬夜。還在念幼兒園的她,又一次被嚴厲的媽媽關在陽台。刺骨的寒風中,從陽台隔板另一端伸出了一隻細細白白的手。他們誰都沒有出聲,只以指尖碰觸彼此,在黑暗中交流。在香得知隔壁家的女孩名叫沙良的時候,香的爸爸卻被發現自殺身亡。香匆匆搬離,甚至來不及和沙良道別。
十多年後,小鎮上發生駭人聽聞的「笹塚町一家殺害事件」──成天繭居在家的哥哥立石力輝斗,在平安夜用菜刀殺死了就讀高三的妹妹立石沙良後,放火燒了房子,讓父母也喪生火窟。
如今,已成為電影導演的香,邀請新人編劇甲斐真尋以這樁舊案為原型撰寫劇本。原本興致缺缺的真尋,因緣際會接觸到案件的關係人後,卻發現了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真相」……
Amazon書店★★★★狂推!日本讀者看完後忍不住讚歎:「最後把所有的伏筆全部收攏起來,不愧是湊佳苗!」「層層疊疊的解謎後是帶有希望的結局,讀完後非常感動!」「非常期待能夠影視化!」
【資深編劇】吳洛纓 專文推薦 【導演】王小棣、【作家】馬欣、【導演】侯季然、【臉書版主】重點就在括號裡、【小說家】陳又津、【導演】鄭文堂 震撼好評!

湊佳苗
一九七三年生於廣島,是日本當前最受矚目的暢銷名家。曾入選二○○五年第二屆「BS-i新人劇本獎」佳作,二○○七年則榮獲第三十五屆「廣播連續劇大獎」,同年又以短篇小說〈神職者〉得到第二十九屆「小說推理新人獎」,而以〈神職者〉作為第一章的長篇小說《告白》於二○○八年獲得《週刊文春》年度十大推理小說第一名,更贏得了二○○九年第六屆「本屋大賞」。二○一二年以〈望鄉、海之星〉獲得第六十五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短篇小說部門獎,二○一六年以《理想國》榮獲第二十九屆「山本周五郎賞」,二○一八年再以《贖罪》入圍世界推理文壇最高榮譽「愛倫坡獎」。
出人意表的爭議情節,引人入勝的文字功力,以及闔上書之後仍令人反芻再三的懸疑餘韻和人性掙扎,是她的作品能夠博得讀者和評論家一致好評的最大魅力所在,被譽為「黑暗系小說女王」。
她的作品也是熱門的影視改編對象,除了《告白》外,《贖罪》、《白雪公主殺人事件》、《為了N》、《少女》、《望鄉》、《反轉》和《惡毒女兒.聖潔母親》也陸續被改編拍成電影或電視劇,備受好評。
另著有《碎片》、《未來》、《藍寶石》、《母性》等書。

我回想起她白白的手。我忘不了她指尖的溫度、感覺,和曾經交流的心。
我至今仍然不認為那是虐待。
那只是管教。當時我這麼認為,媽媽也這麼說。但也許是媽媽這麼說,我才這麼認為。
爸爸、媽媽從來沒有對我動過手,但媽媽經常發脾氣。每當我打翻杯子裡的水,或是畫完畫之後,沒有把蠟筆放回盒子裡,媽媽就會大聲斥責「要說幾次才聽得懂」、「別再惹我生氣了」。
但是,我並不是因為這些原因被趕去陽臺。
從上幼兒園的那一年開始,每天吃完晚餐,就是我的「寫功課時間」,寫國文、算數和英文三個科目的習題。最初寫一些遊戲性質的學齡前兒童習題集,但小班的暑假之後就開始進階,升上大班之前,我已經完成了小學二年級生用的習題集。
我讀的並不是將來要報考名門小學的私立幼兒園,那時候住的地方根本和名校沾不上邊,也沒有私立小學,更沒有地方可以炫耀記住的漢字、英文單字或是九九乘法表。
所以我開始覺得有點奇怪。
我從來沒有寫過功課。九九乘法表不是上了小學之後才要學嗎?
也許是因為我周圍所有的同學都這麼回答我內心的小小疑問,所以我才覺得我們家可能有點與眾不同。但無論在任何團體內,即使是鄉下地方的公立幼兒園,也總會有一、兩個與眾不同的孩子。比方說,在進幼兒園之前就已經會背九九乘法表,還能夠記住一百年之後年曆的正隆,還有只要看一次樂譜,就可以完全背下來,然後按照樂譜彈鋼琴的千穗。
並不是只有我與眾不同而已,相反地,和他們相比,我所做的只是很普通的讀書而已,根本稱不上是與眾不同的孩子。
至少不符合媽媽的期望……
所以,我被關在陽臺也無話可說。
我沒辦法記住,所以是我的錯。是我太笨了,所以是我的錯。如果全都答對,媽媽就會眉開眼笑地稱讚我。妳看,得一百分是不是很高興?媽媽會這麼對我說,然後溫柔地撫摸我的頭。
但是,我的腦袋並沒有那麼聰明,無法過目不忘。也不是任何內容只要連續寫十次,就可以記得一清二楚。即使我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也無法把所看的內容印在腦海中。
第一次在十題中錯了超過三題的那一天,媽媽把紅筆用力往桌上一丟,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後站了起來,滿臉痛心地皺起眉頭,幽幽地說:
「妳給我出去。」
出去?是叫我離開這個房間的意思嗎?從這個兩房一廳的客廳去其他房間的意思嗎?我沒有自己的房間,家裡的兩個房間分別是全家人一起睡覺的臥室,和放衣櫃和其他雜物的儲藏室。
雖然我沒有立刻走出客廳,但知道遭到了媽媽的拒絕。惹媽媽生氣讓我感到難過,讓媽媽失望讓我感到愧疚,眼淚從瞪大的眼睛中流了下來。媽媽比剛才更大聲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就像是畫上一個逗點似地咂了一下嘴說:
「媽媽最討厭哭哭啼啼的小孩,腦袋不靈光的小孩動不動就哭,因為他們沒辦法用言語說明。」
眼淚這種東西,並不是說停就能停下來,但我覺得不能再哭了,所以用雙手拚命擦著眼淚,結果媽媽用力抓著我的手臂往上拉。我被她拉了起來,然後她就推我的後背。我沒有反抗,被她推著往前走,眼前的落地窗打開,我感受到後背被用力一推,然後就獨自留在陽臺上,落地窗在我身後呯地一聲關上了。
隨即又聽到了有點卡住的鎖被鎖上的聲音,接著,嘩地一聲,連窗簾也拉了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被關在陽臺上。
那時候的氣候既不熱,也不冷,如果是為了看星星走到陽臺上,即使在陽臺上一整晚也沒關係,但違反自己意志被關在陽臺上,就覺得那是一個令人極度不安的地方。
幼兒園教室後方的書架上最角落有一本沒什麼人看的繪本,其中一頁是森林中的可怕池沼中有一艘小船。我覺得自己好像坐在那艘小船上搖晃,難道是因為那一頁上寫的「那是一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漆黑夜晚」這句話,和我抬頭看到陽臺外的夜空一樣的關係?
第一天、第一次往往決定了日後的命運。這句話似乎也符合當時的情況,如果我被關在陽臺上因為感到恐懼而哇哇大哭,是否就會變成僅此一次,下不為例?距今三十年前,在那種鄉下地方,大家都還很愛管閒事。
但是,我一心不想惹媽媽討厭。聽到媽媽說,最討厭愛哭的孩子,當然不可能哭得比剛才更兇。人……至少是我這個人,為什麼感到不安的時候,就會縮成一團?
現在身為一個影視工作者,我猜想這個動作可能投射了內心希望自己消失的願望,但也可能只是不希望別人看到我的糗樣,或是可能源自潛在的防衛本能,努力縮小表面積,消除自己的動靜,保護自己不受包括酷暑、寒冷等天氣因素在內的外敵攻擊。
由於第一次發生時我沒有抵抗,那天之後,只要寫功課的正確率低於七成,就會被關去陽臺,漸漸變成了一種習慣。每個星期有一次,多的時候會有兩次。我被關在陽臺上的時間通常都是晚上八、九點左右,所以每天十點多才回家的爸爸,有很長一段時間並不知道這件事。即使如此,爸爸似乎對媽媽熱心地要求我讀書這件事頗有微詞。
有一天晚上,當我躺在被子裡時,聽到爸爸、媽媽在紙拉門外的對話。
「現在不需要把孩子逼得這麼緊,讓她開開心心長大不是比較好嗎?」
「在鄉下地方開開心心長大的結果,就會輸在起跑點,失去競爭力,你要怎麼負責?到時候是我被人看不起。如果你有意見,等你讓我們擺脫這種生活之後再說。」
爸爸沒有再說一句話。
雖然被關在陽臺上很痛苦,但我之所以沒有向爸爸求助,是因為即使沒有聽到他們之間這樣的對話,我也預料到爸爸根本不值得期待。
爸爸從來沒有罵過我。我這麼告訴幼兒園的同學,大家都說:「妳爸爸真是好脾氣。」有很長一段時間,別人問我爸爸是怎樣的人,我都回答說,他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但也許事實並非如此。
他只是漠不關心。但這並不是壞事。
我之所以會這麼想,是因為我現在還活著的關係嗎?還是我知道有人比我境遇更慘的關係?
即使季節改變,只要寫習題的正確率達不到七成的日子,我就會被關在陽臺上。無論酷暑的日子、下雨天,還是寒冬的日子都一樣,但我已經不會像起初那麼痛苦了。因為我知道,只要被關在外面一個小時,媽媽就會讓我進去。之後媽媽雖然不會對我特別溫柔,但也不會再挨罵,通常都叫我去洗澡,然後一天就結束,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反正習慣就好。不僅如此,而且我發現在陽臺上可以聽到平時無法瞭解的、別人家的生活動靜,然後想像這棟公寓住了哪些鄰居,漸漸變成一件開心的事。
雖然媽媽經常很不滿地抱怨,這棟每個樓層有六戶住戶的三層樓公寓是破公寓,但其實不太聽得到隔壁人家的動靜。雖然有時候會感受到一些震動,但聽不清楚說話的內容,也聽不到隔壁住戶家電視的聲音。
兩個月前,住在右側的那戶人家搬走了,一個月後,又有新的住戶搬進來。媽媽在門口遇到了新鄰居之前,根本沒有察覺這件事。
但是我知道,每次被關在陽臺上聽到的西洋音樂,從某個時間點之後,變成了綜藝節目特有的笑容。
然後,就到了那一天。
我實在無法理解乘法的筆算,又被關去陽臺了。只有那一天,聽到媽媽說「妳給我出去」時,我露出懷疑的眼神看著媽媽,因為從幼兒園回家的路上,天空就飄著雪。
打開落地窗,看到夜空中仍然飄著雪,但難道是因為外面並沒有積雪,所以媽媽才沒有說「今天就算了」嗎?還是覺得我穿了毛衣,所以認為我不會凍死?
我在每次被關在陽臺上時相同的位置,也就是陽臺的正中央,背靠著落地窗,雙手抱膝坐在那裡等待,但那天實在太冷了。後背一碰到玻璃,就好像靠在冰牆上,一股寒意貫穿脖頸,而且風也不停地灌進來。
竟然把我關在這種地方、竟然把我關在這種地方……如果淚水湧上眼眶,我或許會哭喊著敲打落地窗,就像不久之前在連續劇中看到的那個女人,想要挽留為無聊的事爭吵後準備衝出家門的男友一樣。
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個人,你不要不喜歡我。如果我也能這樣直接說出我的感情,媽媽就會像連續劇中的那對情侶一樣走到我身邊,然後緊緊抱著我嗎?
討論這種幾十年前的假設毫無意義。
總之,我當時並沒有叫喊,而是在陽臺上尋找可以避風的地方。結果發現空調室外機和隔壁陽臺的隔板之間,有一個不到一公尺的間隙,而且正在運轉的室外機持續送出暖風。
我靠在水泥牆壁上,抱著膝蓋坐在那裡。雖然水泥牆壁不像玻璃那麼冰,但還是很冷。縮起脖子時,無法仰頭看天空。當我將眼珠子轉向旁邊時,看到隔板中央附近寫的小字。
「遇到緊急狀況時,請打破此隔板逃生」
雖然我當時已經開始學漢字,但現在已經想不起當時是否能夠看懂「緊急」、「逃生」這些字,但應該從「打破」這兩個字猜到了意思。
要怎麼打破看起來很堅固的乳白色隔板?用力敲?還是用力踹?或是用椅子之類的東西砸破嗎?如果真的這麼做,隔壁鄰居一定會嚇壞,還可能會破口大罵:「怎麼可以破壞隔板,擅自闖進我家!」所以除非真的遇到了讓人覺得不得已的狀況,否則不可以隨便打破。
到底是怎樣的狀況才能稱為不得已?有強盜闖進家裡,拿著菜刀追殺嗎?不,只有電視裡會發生這種狀況。
對了,火災。如果在客廳時,看到廚房著火,就無法從大門逃出去,所以就衝去陽臺,打破這塊隔板,向隔壁鄰居求助……差不多像是這樣的狀況嗎?大喊著「打擾一下」,用力敲打鄰居家的落地窗,請鄰居打開落地窗。但如果鄰居不在家呢?那就要再打破鄰居家和鄰居的鄰居家之間的隔板嗎?如果鄰居的鄰居也不在家呢?如果同一個樓層都沒有人在家呢?到了這個樓層的盡頭,最後要怎麼辦……?
是因為我一直想著隔板另一端的事,所以才會發現?還是因為太在意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好幾塊隔板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才會沒有馬上察覺到眼前這塊隔板另一端的動靜?
即使看著隔板,也無法透視,既然這樣,能不能從下方看到什麼?我這麼想著,將視線向下移動……然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氣。因為陽臺的底板和隔板之間有大約十公分的縫隙,我發現那裡有一隻手。
我嚇了一跳,卻無法發出聲音。我不僅學會了不哭,受到驚嚇時也不會立刻發出驚叫聲。即使笑的時候,也不會噗哧一聲笑出來,更不會因為恐懼大叫。
但是,我並沒有感到害怕。那並不是幽靈的手。有人在隔板的另一端。那隻手和我差不多大小,不,手指可能比我的更纖細。那隻手很白,只不過指甲很髒,有點長。而且,那隻手在微微發抖?
她也和我一樣,因為惹父母生氣,讓父母失望,所以被關在陽臺上嗎?也許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才會害怕,才會難過得發抖。
她想告訴我,我並不孤單嗎?不,我只是為得到了可以壯膽的同伴感到很高興。我想告訴她自己的存在。只要我伸出手,就可以碰觸到那隻手,但絕對不是因為覺得那隻手髒,所以才無法伸出手。
我很怕別人碰我。比方說,老師要求我們和旁邊的人牽手時,我可以伸出手,並不會覺得討厭,但突然被人握住手,就會馬上甩開對方的手,然後把手放進口袋,好像要讓自己的手避難。
我也因為這個原因開始被幼兒園的同學討厭,被人在背後說自以為是小公主、很自大,就連老師也來提醒我。之後花了幾年的歲月,才能夠用言語說明,其實我只是需要一點心理準備,只是要在心情上針對這個行為做好調適。也許我至今仍然沒有克服這個問題。
雖然沒有任何根據,但我覺得那隻小手的主人和我很像。即使我碰觸那隻小手想要鼓勵她,她可能也會縮手。
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這個行為本身的選擇並沒有錯。即使對方是很開朗活潑的女生,如果有人在黑暗中突然碰她的手,她一定會嚇得縮手。
既然這樣,要怎麼告訴她,我也在這裡呢?
我坐在那裡伸出手,用指尖在比我的肩膀稍高,剛好在我耳朵位置的隔板上咚咚咚地敲了三下。視線仍然看著下方。這時,我看到那隻手的指尖抖了一下。她似乎聽到了動靜。
然後,我跪著調整了身體的方向,把手撐在從隔板下方露出那隻手的旁邊,再用另一隻手的指尖在隔板下方,就在撐在地上那隻手稍微上面的位置咚咚咚敲了三下。
希望在隔板另一端的她可以看到我的手。希望她在發現隔牆似乎有人而產生緊張之後,知道在隔板的另一端是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孩子,能夠放鬆緊張。
隔板下方的那隻手微微抬了起來,中指好像在彈鋼琴一樣,在陽臺底部冰冷的水泥上咚咚咚敲了三下。
聽、到、了。
我覺得她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我的手指也重複了相同的動作。對方又咚咚咚敲了三下,我又敲了三下。不知道重複了幾次之後,彼此的指尖輕輕碰觸了一下。既不覺得她的手指冰,也不覺得溫暖,是因為我們的手指都一樣冰嗎?只覺得指尖很癢。在覺得有點癢的同時指尖相碰後,我覺得兩個人好像都在笑。
不知道她是怎樣的女生?我很想和她聊天,但我不敢開口和她說話,因為會被媽媽聽到,也會被她的家人聽到。
我握起了原本晃動的手指,只留下食指,然後在隔板正下方的水泥地上寫字。
「香」。
我想要向她自我介紹。對方的手停頓了一下,然後靜靜地動了起來,手指寫下五個鋸齒。那不是寫字,而是畫了一顆星星。我對無法和對方順利溝通感到有點納悶,但立刻想到了答案。
隔板另一端的她還不會寫字。我既沒有失望,也沒有覺得她很笨。因為幼兒園也有很多同學不會寫字。有的會讀不會寫,也有的既不會讀,也不會寫。雖然有人會罵那些同學很笨,但那些罵人的同學很快就會被老師罵。
我也動手畫了起來。我畫了三個鋸齒,再加上一個半圓形和一條直線,兩側又畫了兩個橢圓形。我畫的是鬱金香。這次她的手指立刻動了起來。圓圈、三角形、三角形。是貓的臉,左右又各畫了三根鬍鬚,然後是眼睛、鼻子和嘴巴。嘴巴是向下的半圓形,和笑臉標誌一樣。也許在隔板另一端的她也正露出相同的笑臉。
我這麼想像著,準備也送她一張笑臉。正當我準備畫圓時,聽到落地窗打開的聲音。我立刻縮起了手,握起雙手放在膝蓋上,好像在表示我什麼都沒做。
「原來妳在那裡。」
媽媽似乎終於發現我坐在和平時不一樣的地方。
「進來吧。」
如果媽媽走到我面前說這句話,也許會察覺隔板另一側的動靜,但是,媽媽並沒有走到陽臺上。她為冷氣灌進了溫暖的房間皺著眉頭,站在落地窗前催我:「快進來。」
雖然我很想再度輕碰隔板另一端的指尖代替說再見,但如果我磨磨蹭蹭,媽媽可能會關上落地窗,然後鎖起來。我站起來的同時看了一眼那隻白白的手,然後走回了房間。
不知道她被關在陽臺上多久?雖然我很在意這件事,但完全沒想過要把隔壁陽臺上也有一個小孩的事告訴媽媽。難道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快又會被關去陽臺,很希望到時候再遇到她嗎?
過去的記憶雖然變成明確的影像在腦海中重現,但影像中的自己當時到底在想什麼,也許只能回想起五成左右。所以,我對隔板另一端的她所產生的感受,也可能是事後在腦內補充的,即使如此,我仍然相信指尖回想起的感覺就是當時的感受。
我希望可以再遇到她。下次要畫什麼呢?如果我畫恐龍或是鱷魚這種很難的畫,她也許會很驚訝。
那天之後,我在幼兒園的休息時間經常畫畫。
「大家畫恐龍時都畫側面,香香,妳是畫正面欸,好酷喔。」
我忘了是誰對我說這句話。自從在陽臺發生那件事之後,我整天都在想隔板另一端的那個女生,根本不把周圍的同學放在眼裡。我不想只是在水泥上隨便畫一畫恐龍,而是想畫得很逼真。
雖然從那道狹窄的縫隙把信或是畫塞過去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當時還是小孩子的我,覺得不可以在那裡做那種事,不能為我們的交流留下任何證據。
一心不想被媽媽關去陽臺時,有時候連續兩天做功課的正確率都無法達到一半,在覺得即使被關去陽臺也沒關係之後,卻連做連對。這可能意味著我從小的抗壓性都很差。
在腦子完全沒有得獎這件事的時候,好像著了魔似地充滿了想要拍攝的欲望,沒想到不小心得了大獎,聽到別人說,下次一定要得更大獎的聲音之後,腦袋就變成一片空白。
這時,腦海中浮現出這些陽臺上的影像。
即使無法在陽臺上相遇,如果能夠在其他地方,比方說在家門口,或是附近的公園見到她,我絕對不會故意把功課寫錯。不會在算乘法時故意不進位,也不會在寫漢字時故意少寫一橫。我是個笨小孩,可能覺得故意寫錯答案就像是考試作弊。
但是,我在十天之後,又被關去陽臺了,而且媽媽並沒有發現我故意寫錯。那天雖然沒有下雪,但還是很冷,吐出的氣都是白色。我確認媽媽拉起窗簾後,走去室外機旁,在隔板的另一側看到了那隻白白的手。
我在蹲下來的同時,用食指的指尖在隔板上咚咚咚敲了幾下。那隻白白的手抖了一下,這次我用指尖輕輕碰了一下她伸出的手背。她的指甲比上次短了些,只是有點參差不齊,看起來並不是用指尖刀剪的,而是用牙齒咬的。
幼兒園也有同學整天啃大拇指的指甲,所以我猜想她應該也有同樣的習慣,就沒有太在意。指甲參差不齊的那隻手和我一樣豎起了食指,然後咚咚咚敲了三下水泥地。我敲三下是在問她「妳好嗎?」她也和我一樣嗎?
我正在思考該怎麼回答,白白的手指在水泥地上畫了一個圓圈,然後輕輕敲了兩次。接著又畫了一個心形,輕敲了一次。是不是代表這個意思?我畫了星星,輕敲了兩次,又畫了脖子長長的長頸鹿,敲了三次。那隻白白的手將大拇指和食指圈在一起,比了一個OK的手勢。
這是我們之間的摩斯密碼。有形的東西可以畫畫,但心情很難用畫畫表示,所以就靠輕敲的次數猜測相符的詞彙。三次就是「妳好嗎?」如果是四次就是「非常謝謝」,至於兩次……
我想要表達「朋友」的意思,在輕敲了兩次之後,畫了兩個站在的人。
我們像這樣用指尖總共交流了六次。在最後一次的第六次時,我看到她白白的手背上有一個直徑不到一公分大小的紅色水泡。妳怎麼了?這次我忍不住脫口問道,但隔板的另一端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問了這個問題的關係,所以她改變了坐的方向,伸出了沒有受傷的手。
雖然是同一個人的手,卻讓我有一種陌生的感覺。我們只用手交流,兩隻手分別有不同的人格,和我成為好朋友的是大拇指在後方的左手,右手則是初次見面。但她的右手和左手一樣白,指甲也很髒。
我也換了方向,背靠著陽臺欄杆坐了下來,平時都用右手,這次伸出了和平時相反的左手。兩隻初次見面的手沒有像平時一樣聊天,彼此慢慢靠近,起初有點戰戰兢兢,最後用力握在一起。我們握得很用力,可以感受到溫暖一直擴散到指尖。
好想見面,想看看她長什麼樣子。
我要帶著畫,按門鈴去見她。
在我這麼下定決心的隔天,我見到了她。真的只是巧合,彷彿天上的星星聽到了我的心願。
那天傍晚,我跟著媽媽去附近的超市「晴海商店」買菜。走到肉品區時,媽媽對我說,她忘記買牛奶了,叫我去拿一瓶牛奶。我走回乳製品區,拿了一盒平時媽媽常買品牌的一公升裝牛奶,走回肉品區,看到媽媽正面帶笑容,對著站在她前方的一對母女微微鞠躬。
那個女人和媽媽差不多年紀,衣著很花俏,身旁的女生和我年紀差不多,頭上綁了一個很大的蝴蝶結。穿著附近一家托兒所的藍色罩衣。
我躲在媽媽身後,悄悄把牛奶放進推車上的購物籃內,媽媽轉過頭,露出眼睛完全沒有笑意的笑容對我說:
「香,這是住在我們隔壁的立石太太,妳來打聲招呼。沙良和妳同年,已經會自我介紹了。」
隔壁的……我無法吞下倒吸的那一口氣,看著名叫沙良的女孩。她皮膚很白,有一雙圓滾滾的大眼睛。可愛的樣子簡直可以上電視。
沙良對我嫣然一笑,好像我們是認識已久的朋友。她的雙眼露出了調皮的眼神,好像在說,我們早就認識了。
我也想回報像她那樣的笑容,但應該變成了只有嘴角上揚的不自然表情,事後媽媽一定會罵我冷冰冰,但這就是我的笑容,我也無可奈何。
媽媽似乎無意和屬於不同類型的鄰居太太當朋友,聽到我說「阿姨好」之後,就說了聲「那我先走了」,推著推車離開了。
沙良揮手對我說「拜拜」,我也向她揮了揮手。當我們擦身而過之後,我才想起她手上的傷。回頭一看,發現沙良和她媽媽仍然在直線的延長線上,但我看不到她的手背。
因為沙良和她媽媽牽著手。她的媽媽單手推著推車。我這才發現「我手上有很多東西」、「我很忙」無法成為不牽手的理由,但我也不會主動去握住媽媽雙手推著推車的手。
我的手上之所以還可以感受到沙良小手的感覺,除了在我痛苦的時候曾經激勵我以外,更因為在她之後,不曾有任何人像她那麼用心地以手和我交流,取代這份記憶。
在我見到沙良那一週的週末,偶爾會和我牽手的爸爸自殺了。
我知道即使不去陽臺也可以見到沙良,但我讀的是三點就放學的幼兒園,沙良讀的是托兒所。即使我有勇氣去按她家的門鈴,非假日也見不到她。於是我決定等到週末。
星期六下午,爸爸說他要出門看電影。他常在週末去看電影。我下午要寫功課,這也和平時的週末一樣,但那天媽媽心情特別差,要我寫的功課比平時多了一倍。
今天沒辦法和沙良一起玩了,明天的話……夜深之後,這份期待也落了空。因為有人在海裡發現了爸爸的屍體。
媽媽和我一起搬去了媽媽娘家的外婆家裡。
我無法向沙良道別。在公寓度過的最後一個晚上,我趁媽媽洗澡的時候去了陽臺,但在陽臺的隔板下沒有看到那隻白白的手。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不是在隔板或是水泥地上,而是用指尖在她白白的手背上輕輕敲兩下。
再、見。
於是,沙良就會依依不捨,但很溫柔地向我揮手道別。我也會向她揮手。接著,兩個人的指尖會像在相互搔癢般交纏在一起,用力握一下手。雖然依依不捨,但我會鬆開她的手,最後再輕輕在她的手背上敲六下。我相信沙良一定能夠瞭解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我、不、會、忘、記、妳。
雖然無法這麼做,但我在隔天早上離開之前,把一封簡短的信放進了沙良家的信箱裡。我並沒有留下新的地址,但我充滿真心誠意地在信上寫著——
「好想再見到妳」。
那天之後,我並沒有每天都想到沙良,甚至幾乎忘記了她。但是……
在想要一死了之,而且最好身首異處的時候。
我曾經想像跳向迎面而來的電車,血肉模糊、內臟四濺。但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流血的量、手腳斷裂的方式都只是想像力能夠承受的驚悚,所以才會在最後的畫面中呈現電車經過的鐵軌上,留下剛好在手腕處斷裂的右手。
宛如只有那個部分依然是純潔無瑕的我。
但是,我沒有勇氣跳向電車。並不是因為我用這種方式死去,家人會為我感到難過,而是想到他們還必須費心為我造成很多人的困擾善後。
所以我也曾經用美工刀放在手腕上。只要稍微用力就好。我這麼想著,用力閉上眼睛。不知道為什麼,指尖感到很癢。
不要,不要,沙良。
自從搬離那棟公寓之後,即使會回想起指尖熟悉的感覺,但那是第一次想起她的名字。那時候是十五歲,所以是相隔十年想起她的名字。
三年後的十八歲,在我不時閃過自殺念頭的那一陣子,沙良遭到了殺害。
然後就這樣過了十五年的歲月——
十五年後,已成為電影導演的香,邀請新人編劇甲斐真尋以這樁舊案為原型撰寫劇本。她們會發現什麼樣的真相,又如何面對不想面對的過去呢?